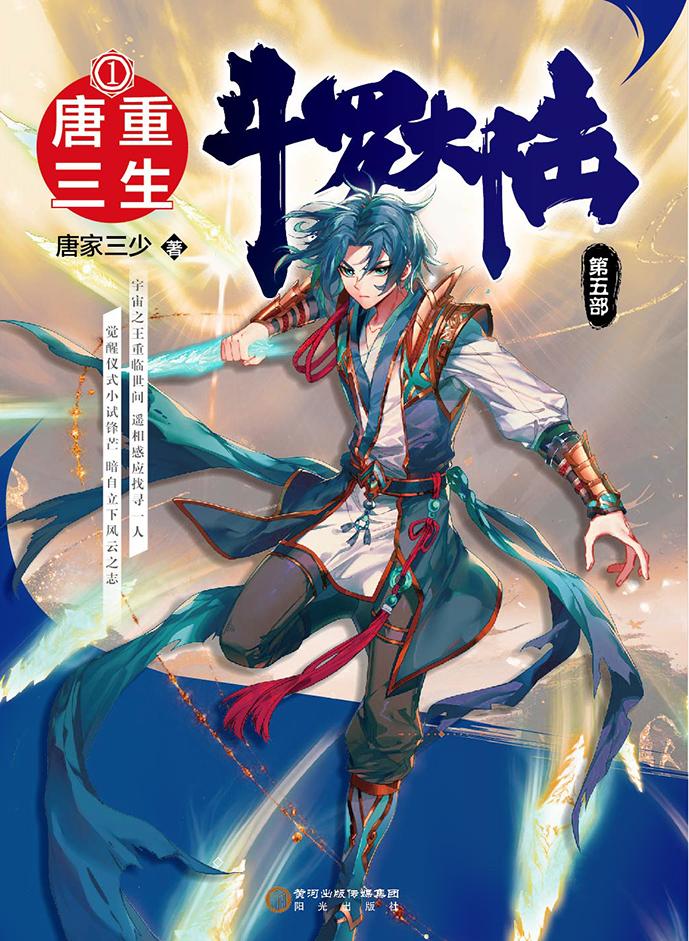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犬夜叉之辰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他不经意间缓和了神色,微微点头:“不错。那南国不过是仗着公主桫椤的妖法,只要我杀了那个女人,就能一举夺回西南众地。之后,我再灭了东国和北国,整个妖界便再无需受战乱之苦。”
桔梗定定地看着他。她清楚凭他的能耐,终是会成就大事的。只是她心里一丝隐忧难除。她这番话是为了众生安宁,却不知他究竟是否明白。
是夜,清冷的月光洒下银白,好像把冬夜里仅存的几丝温度都抽离了。
至少,当奈落坐在冰冷的石阶上灌酒的时候,那刺骨的冰寒始终化不去。
他俊逸的面容此刻蒙上一层阴翳,一双眼中布满了血丝。某种愤恨而不甘的神情攫住了他,竟给他本是严峻的面孔平添了几分邪气。
烈酒烧喉,他只觉胸口滞闷无比,紧攥着酒杯的手无法抑制地微颤。心中恼恨,他狠狠一掷,那杯子跌在地上碎作几瓣。
“师哥竟也会一个人喝闷酒?”
身侧一个冷冷的声儿响起,他鼻下一哼,头也不抬:“你来这里做什么?”
桩低头冷眼看着他:“师父不喜欢人饮酒无度,你这样可会惹他老人家不高兴的。”
“这关你什么事。”他站起身来,一脚把地上的酒坛踢翻,空气中泛起浓烈的酒香,“我喝我的酒,师父要罚就让他罚去。”
他说罢便要拂袖离去,被她一把拉住衣袖。
“你要做什么?”他冷语,连正眼都不瞧她一下。
桩眼中闪着异样的光,直勾勾地盯着他:“师哥,你对桔师妹那么好,对我就连一句话也不愿听么?”
一听到桔梗的名字,他眼神瞬间冰冷了。
“师哥,我真是为你不值。”桩邪魅一笑,“你是师父的大弟子,却受制于祖训叫我忝居了掌门的位子。这也就罢了,可师父他,连心法也不肯授给你。你空有一身本事,只落得个形同虚设的辅灵,太亏了。”
他一言不发,双手却握紧了。
她靠近他,挨上他的身子:“师哥,你也不为自己考虑考虑。我知道你待桔师妹一往情深,可她呢,不冷不热的,总摆出一副清高样儿来。她得了心法,可有透露给你一丝一毫?你心里有她,可她心里不一定有你啊——”
“够了!”他嘶哑了嗓子吼道。他恨恨地看着身侧的女人,她如何知道他心里有多少怨愤?自从他清早瞧见桔梗脖颈上的伤,她遮掩般的回答便叫他起了疑心。他暗自猜想了千样万样缘由,却全都抵不上他亲眼所见时那锥心的震颤。
桩冷笑一下,换上平素那一副冷淡神色:“我可是在给你指一条明路。师父百年之后,那白灵心法终究会是由我来守护的。你若明白事理,便该与我一道,以你我二人之力,就不怕解不开守备的结界,到时候,心法还不是你囊中之物么?师哥,你想想,等我做了掌门,什么规矩不都是我说了算?你要是真心喜欢桔师妹,我也可以让她不用出山的。”
奈落没有说话,眼神深不见底。渐渐的,阴翳浮上他的眼瞳,浸染出好像染了血一般的深红来。
“桩,你想拉拢我,可得让我看到你的诚意。”他目光奇寒穿透她眼眸直至心底,“眼下倒有一件事叫我很难办,不知你会不会帮我呢?”
次日当桔梗再次来到那片密林时,她只看到空寂的山林向四面无限延展开去,那棵老榆树下杂乱的草茎是唯一表明这里有人待过的痕迹。
心里竟一时空了片刻。她自然知道那倔强的妖国皇子是绝不会久留于此的,可也没想到他会走得这么急。他还不过是刚刚能起身罢了,只凭着一身傲气,又能走到哪里去,又能走多远呢……
她赶上他的时候,是在西峰崖绝壁下。
凛风卷起他银白得近乎透明的长发,宽大的衣袍在风中猎猎飞扬。她逆着风喊他的名字,寒风混杂着瀑布的轰鸣震得她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但他终是站住了,侧过身来望向她。风从他身后掠过,他因失血而泛白的面孔多了一分奇异的俊美,仿佛是粗粝中罕有的添上了一丝温和。
“杀生丸。”她唤他,他看着她跃过嶙峋的石块趟过漂满浮冰的溪流,冰寒的水沾湿她薄薄的裙裾她脚步却未慢下分毫。
她微微气喘地在他面前站定。他是完全的失神,甚至不知该怎样去面对她这样不顾一切地追赶,以及她脸上一目了然的诘问。
“我得回西国。”他最终这样说,语气是倔强的。
她忿忿地望着他,那眼神叫他心里不禁一颤。
“你就如此信不过我?”她问,“这么急着走,连个告别的时间都不肯留给我?”
金瞳妖眼在她的逼视下微微颤动了下,避开了她的眼睛。
“我没有信不过你,桔梗。”他轻声道。这是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
她扭开头,眼中坚硬的神情微微消融了些。
“你救我一命,我必当回报。”他说,“但我身后有大批南国追兵,他们为了不留后患,所到之处全都烧毁殆尽。我不能再给你带来不必要的祸患——”
某样温暖得出奇的感触截住了他的话。她伸出手来环抱了他。那样安静的,却不容他抗拒的怀抱。
“我不在乎的。”她把头靠在他胸前,“我不在乎什么追兵,什么祸患。我只是不想要你死。”
片刻的畏缩闪过他心头。那一刻他只想逃离,逃离他此时已隐隐预见的,却无力拒绝只能沉沦深陷而不可挽回的一切。
他回抱住了她。
那样的……令人快活。四周的山林好像都化作虚无,鸟鸣渐渐消散,溪水间浮冰融化,晨曦打散林间的雾霭涂抹出暖意的金黄。一时间,白灵也好,西国也罢,全都蒙上了一层雾气,朦朦胧胧看不真切。世间的真实,只是他怀中的女子。仿佛他此生的全部意义就只有她,只能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