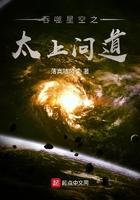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沉溺春雾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笔趣阁 > 5059(第2页)
5059(第2页)
“不是很好。”他淡声回答,又看一眼她埋得极低的脑袋,薄唇勾起浅笑:“但也死不了。”
她这才抬头,眉心紧紧拧着,“你能不能不要总把死这个字挂嘴边。”
语气有点冲,有些凶。
他一个大资本家,怎么就没点忌讳。
听见这话,谢云渡那双平静的黑眸中浮现出淡笑,拇指摩挲着她的手背,懒散应着:“好,不说。”
姜幼眠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又越界了,他的事,她不应该管,也没必要说。
这样不清不楚的牵扯下去,对谁都不好。
她想要抽回手,却被他握得更紧,不敢再动。
一路上,两人再无话。
谢云渡带她回了家。
刚打开门,元宝就摇着尾巴冲了过来,汪汪汪的兴奋叫着。
姜幼眠心中一软,蹲下身将小家伙抱起来,摸着它圆滚滚的脑袋:“是不是想我啦?”
满身疲惫,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元宝亲昵地在她怀中蹭着,小尾巴摇得欢。
即使三年不见,依然还清楚记得小主人的气息,还眷恋着主人的怀抱。
姜幼眠脸上扬起明媚的笑,转头对谢云渡说:“它好像真的长胖了,重了不少。”
谢云渡脱掉身上的大衣,随手挂在衣帽架上,视线凝着她那张清纯素净的小脸,薄唇轻启:“它比你好养。”
姜幼眠:“……”
怎么又扯到她身上来了。
谢云渡接过她手中的元宝,打断一人一狗的亲昵叙旧,嗓音沉沉:“去换衣服。”
她站着不动,脸上的笑意不在,撅嘴说:“我想去看我爷爷。”
男人淡淡挑眉:“所以你想就这样去?”
姜幼眠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衣服和鞋子,被雪水打湿了不少,上面还有泥渍。
确实有些狼狈。
更不适合穿着去看望病人。
她抿了抿唇,默不作声地换了鞋后,凭着记忆,轻车熟路来到衣帽间。
当初装修这房子的时候,谢云渡不仅给她弄了个舞蹈房,还留了衣帽间,每到新季,都会让人送来许多高定衣裙,堆得满满的,有些甚至她连碰都没碰过。
这房子还是老样子,无论是布局还是装潢,连那些摆放的小玩意儿都如三年前一样,位置都没变。
复杂的情绪在一次涌上心间。
姜幼眠强压下心中酸楚,随便找了衣服换上。
右腿时不时的胀疼,难受得很,她干脆坐在地毯上,小心翼翼掀开裤腿,原本白皙无痕的膝盖已经肿了。
她为了来见谢云渡,不顾腿疼而奔波,走了好远的路,加上又是寒冷潮湿天气,腿伤复发了。
不过,这种程度的疼她还是能忍的。
和三年那个娇作的姜幼眠不同,她没那么娇气了。
咬咬牙,她又缓慢地将裤腿放下去,捋平,看不出异样。
姜幼眠换好衣服出来时,见谢云渡正在阳台抽烟。
他斜倚着栏杆,身形修长挺拔,身上的西装纹丝不乱,骨节分明的手指微微弯曲,夹着烟,指尖的烟蒂燃着一点猩红,烟雾自他唇间缓缓溢出,掠过那低垂的眉眼。
清冷中带着一丝颓唐。
她记得他以前是不抽烟的。
甚至连烟味都闻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