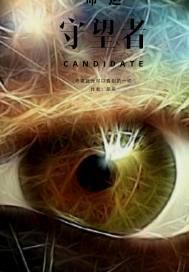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长风望春京香草芋圆的创作背景和创作背景介绍 > 3040(第14页)
3040(第14页)
他把雨伞收拢放置整齐,走过门槛,并不接她的话,只问:“傅母人在何处。”
并未特意遮掩的冷淡态度,章晗玉哪有看不出的。
好好好,回门当天,进章家门就开始摆脸色是吧。
她原本想喊人送茶水的,茶也不喊了,起身道:“傅母那尊大佛可不易请,我去看看,稍候。”
你慢慢等着罢。
把人晾在会客厅堂里干等着,她自己径直穿过夹道去后头内堂。
阮惜罗在佛堂外踌躇不前。
一门之隔,整日把自己关在佛堂里吃斋念佛的傅母,于惜罗来说,比洪水猛兽更可怕。
洪水猛兽还可能降服,但章家这位傅母,实在叫她百般为难。
章晗玉走来佛堂前时,阮惜罗鼓足勇气,刚刚敲开了佛堂窄门,站在门外转述“凌家女婿回门”的消息,邀傅母去往前堂会客。
傅母站在门里。
雨天天光不好,看不清傅母的整张脸庞,只见她的眉梢明显地抽动几下。应是看见远远走来的章晗玉,也看清她身上的穿戴了。
章晗玉索性迎着晨光走去佛堂正对面,让傅母看个清楚。
傅母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她挽起的发髻、身上穿的海棠色对襟上襦、妃色长裙,最后尖锐地停在耳垂新穿的耳洞处。一对明珠耳珰在风里微微晃动不休。
“看清楚了?”章晗玉停在佛堂门外。
“傅母看清楚了孩儿,出去见见人罢。国之四柱,政事堂副相凌凤池,论家世门第,官职前程,难道不是傅母想要的女婿?”
雨丝在长檐飞溅,溅去两人衣襟。
傅母嘴唇抖动几下,似乎想说什么,终究忍住没有说,把门拉开,转身当先入佛堂。
“进来。”
惜罗紧张地抓住主家的手。章晗玉安抚地拍拍惜罗,脱鞋进佛堂。
佛堂终年青烟缭绕。
当中供奉灵位的一座佛龛,擦拭得纤尘不染。
佛母站在佛龛前,凝视片刻,不回头地道:“跪下,给你过世的父母敬香。”
佛堂迎门居中供奉一座观音千手玉佛。转去佛堂背后,背对着门供奉的第二处龛笼,上下三层,供奉的全是章家牌位。
章晗玉接过线香点燃,转去佛堂背后,举过额顶,凝望向龛笼中众多灵位。
京兆章氏全族获罪,流放岭南,那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故事了。
许多族人锦衣玉食地长大,哪受得了流放的罪?不等长途跋涉到流放地,中途便陆陆续续传来死讯。
傅母在京兆附近的县乡住下,隐姓埋名,带年幼的她艰难度日。每个月入一次京城打探消息。回来时,佛堂往往便多一两个牌位。
那时候的她才几岁,四岁,五岁?总之,刚开始记事的年纪,这座伴随她长大的佛堂,简直成了她的童年噩梦。
年幼的她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佛堂里添了新的牌位,她就得跪木牌?为什么活人没吃没喝,却要花大钱给死人做鎏金烫字的牌位?
为什么傅母自己痛哭不止,一边又逼着她哭。她为什么要哭?阿父阿娘人都不在了,她心里记着他们就好,对着木牌哭给谁看?
她不哭,傅母用藤条愤怒打她,骂她不孝。
她反抗过,辩驳过,对骂过。还试图把藤条偷偷藏起来,剪断,扔去院墙外头。
每次的反抗都招来更狠的一顿打。
后来,她学会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势不对就跑。
跑到郊县田埂里躲着,傅母整个白天找不到人,心慌害怕了,大晚上提着灯笼,扯着嗓子喊她的乳名四处寻她。
她蹲在黑暗里看着,就不应。
等傅母找得筋疲力尽,绝望坐倒在深夜漆黑的田埂间哭得死去活来,她才静悄悄地现身,仿佛幽魂一般走近她面前。
傅母自然顾不上打她了,往往会抱住她大哭一场。
年幼的她便知道,这场折腾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