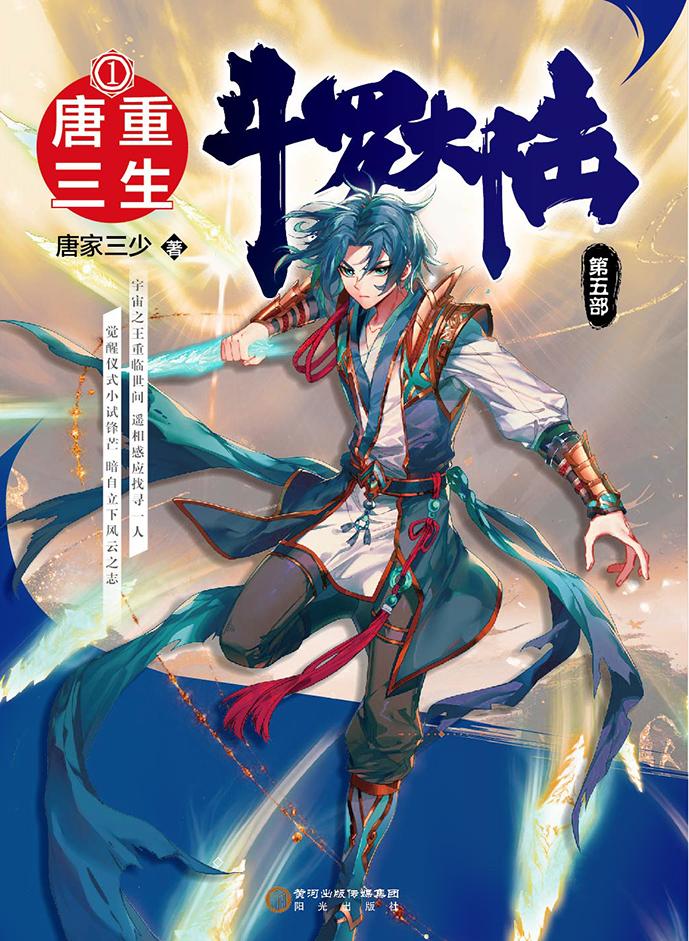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救场演示仅此一次笔趣阁最新章节列表 > 27杀死汉武帝2(第2页)
27杀死汉武帝2(第2页)
大伯说她疯魔了,可是怀都怀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坚称,这是伯娘没有谋取到西厢房间的阴谋,她生的两个儿子,如今还挤在一间房中,她生的女儿已经开始织布,且占了一间房,凭什么大房还要生!因此,母亲和父亲最近晚上都睡得有些晚,争取再生一个孩子,不能吃亏。
重新定义吃亏。
随便吧,这几年,大房、三房都有怀孕生子,生下来随便养着,能活就活,死剩下的再说分房子。
和年轻人的变化相比,大父的变化就小很多,只是脸上沟壑更深,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少。
家里最大的变化是后院新养了一头牛,这是家里最贵重的财产。李老汉不肯使唤狠了,农忙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是喂牛,等牛吃好了,人才开始吃饭。
割牛草、喂牛、打扫牛圈是二哥、三弟、四弟的事情,每次路过牛棚都要从西厢过。李茉为了遮挡牛棚的气味,用破陶罐当花盆,养了几盆茉莉,放在窗边。每次路过,总有芬芳萦绕鼻尖。
二哥今天又从窗前走过,小声嘀咕道:“我看大丫嘴上有油,是不是偷藏好吃的了?”
“油?”三弟、四弟像捕捉到关键字的大鹅,立刻伸长脖子往里面看。
三人扒在窗户上,拨开碍事的茉莉花叶,往里面瞧。
当面就是一大架织机,三颗头换着方向使劲看,怎么也看不清。
“我去前面推门!”三弟立刻想到办法,今天姑姑又带着大丫出门换布,不在家里。
不一会儿,三弟垂头丧气回来,“门关死了。”
“翻窗进去,我看到门边的桌子上,有个漆盒,好吃的肯定在里面!”二哥给两个小弟弟使眼色,三人齐心协力,先把碍事的茉莉花搬开,你帮我我帮你的从窗户里翻进来,着急忙慌绕过织机,去看那漆盒。
也不知是谁先腿绕腿绊了一跤,总之三个人滚做一团,撞在织机上,织机顿时断了一根横梁,当场散架。
三个人都傻了!织机,这是除了牛之外,家里第二贵重的财产,居然让他们弄坏了!怎么办?怎么办?
“不是我,我走在最前面!”
“不是我,我没撞到织机!”
“不是我!我最后进来,织机已经坏了!”
三个人都没闯祸的经验,当场争辩起谁对谁错,吵不出个结果。
正在争辩的时候,姑姑牵着李茉回来,李茉高声尖叫:“啊——织机坏了!”
当天下午,从地里回来的大人们面沉如水,三个闯祸精跪在正堂里,伯娘和母亲正狠狠骂他们,气狠了还要上手捶打几下。两个女人动静大,可耳朵都竖得高高的,关注着西屋的动静。
西屋,大父、大伯、父亲、大哥四人合力,努力把织机修好,终于拼出个样子,大父惊喜道:“试试!”
姑姑坐到织机前,一拉,啦擦一声,刚刚复原的织机又散架了。
所有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沉默在西屋里蔓延。
父亲喃呢:“买新的多少钱?”
大伯反对:“说不定能修好。”
“只有县里有修织机的大匠。”大哥嘴上建议,心里却在打鼓,今秋他就要成亲了,不管织机是买是修,总要用钱,他娶亲可怎么办?
大父的眉心更是竖了三道杠,他计划得好好的,今年大孙子成亲后,在牛棚旁再起一间房,现在,什么都完了。
大父冲进正屋,操起门后的扫帚,狠狠在三个孙子身上抽,不是两个当娘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样子,而是发泄愤怒的狠狠抽打,三个男孩儿立刻放声哭嚎起来!
伯娘挺着大肚子过来拦,“阿翁,打死他们又如何?要是织机能修好,当场打死我也不说半个字!”
正堂又是一阵沉默,三个闯祸精的哭嚎声也渐渐消了,在这么压抑的环境里,他们不敢哭得太大声。
此时此刻,一直缩在阴影里的姑姑走出来,“我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