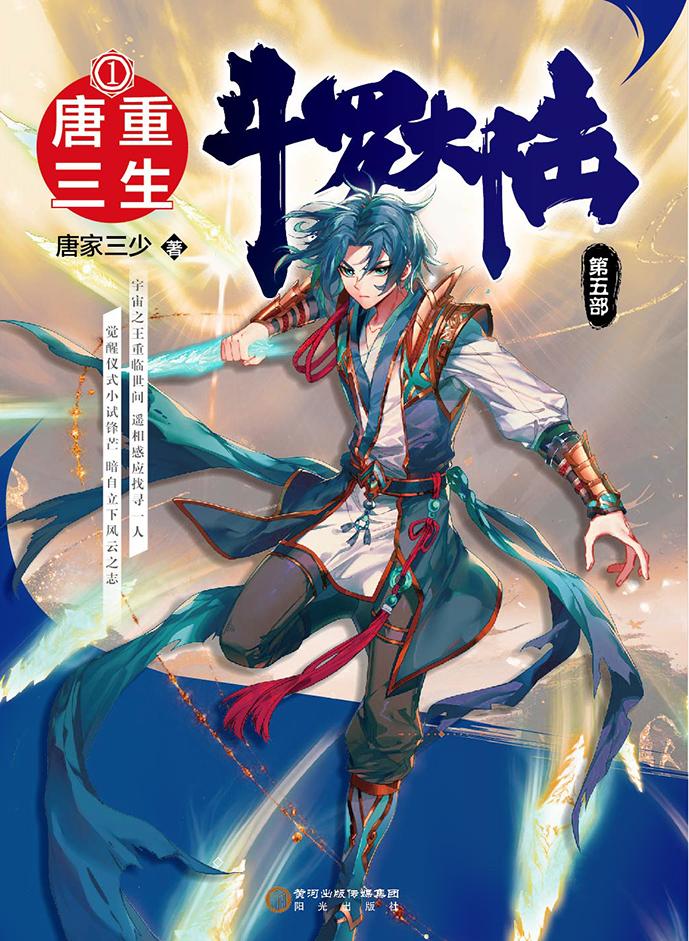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当我另嫁他时by顾景熙讲的什么 > 2第 2 章(第1页)
2第 2 章(第1页)
平旦时分,已是春耕之时,长安郊外不少农户已经起身开始农忙,小院的门被人敲响。
刚刚趴在榻前浅眠过去的徽音被这声音惊醒,她撑着半边发麻的身体跪坐起来,只觉得脑内混沌不堪。
宋夫人安详的躺在榻上,脸上盖着白布,宋景川蜷缩在她脚边熟睡,徽音取过一旁的掉落的被衾覆在他的身上。
初春时节,寒气未散,屋中火塘不知何时熄灭,徽音点燃陶灯,起身将右侧橱下的柴草秸秆抱出来点燃,火塘燃起,驱散一室寒意。
天带着一丝蒙蒙亮,徽音裹着厚厚的粗麻外衣出了门,院子里无灯,她摸索着打开木门,门外立着一张熟悉的面庞,是她的乳母颜娘。
宋府落败后,徽音还了颜娘自由身,将身契交给她让其离开。颜娘却不愿意,她本是长安东郊村落的农女,及笄之后由父亲做主嫁给邻村的的农户。
那汉子是个贪懒爱赌的,不过三年就将家当输个精光,连刚出生的女儿也被活生生饿死,她冷了心肠没了活路,幸得宋夫人路过,将她救下,又将她指给徽音做傅母。
月前宋家败落,她带着身契匆匆去往县延消了奴籍,又匆匆赶回长安。
颜娘一身粗布短打,圆脸厚唇,头发用巾帻严严实实裹在脑后,身形矮胖。
她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肩上还挽着一个布包,人却精神炯炯。一见徽音面上就带起笑容,“女郎,奴回来了。”
徽音一夜未眠,此刻眼下青黑一片,紧绷的心情在看见颜娘的这一刻松懈下来,她强忍着胸口的酸涩,“傅母……阿母她……昨夜去了。”
颜娘笑容僵在脸上,肩上的布包坠地,发出“啪嗒”的声响,她手无措的伸出又收回,只能看着徽音的泪光艰难安慰:“女郎,节哀。”
徽音侧开身,带着她进入屋内,宋景川已经醒了,立在桌前望着二人,眼底还泛着红血丝。
颜娘扑到榻前,宋夫人已经浑身冰凉,她掀起白布看了一眼,心中大恸,捶着胸口流泪,“夫人,您怎么不等等奴就走了啊!”
哭声一出,徽音和宋景川也忍不住,跪在颜娘身侧垂泪。颜娘哭了一会后,抹干眼泪,跪在地上对着宋夫人的尸身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
“夫人,您放心去吧,奴一定会照顾好和女郎和小郎君,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们,逢凶化吉。”
颜娘转身询问徽音二人,“女郎,小郎君,夫人的身后事如何办?”
徽音麻木的接话,“阿母留有遗言,让我们把她和阿父葬在一处。”
颜娘神色哀痛,“南山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无人打扰。”
——
晨鼓一响,徽音便用身上的余钱购置了一套松木棺墩,又扯了两匹白布简单的做了三身丧服,租了辆辎车,带着宋景川和颜娘扶棺出门,一路朝南山行去。
宣平门这处的街道要比旁处略小些,约莫宽八丈,用黄土压得严严实实,两侧挖着暗渠,雨后方过,正涓涓排着污水。
这处近郊,多是庶民农户出行,道路上并未有太多官吏车马行过。两侧小食贩子的木板车已安置好,商贩已经扯着嗓子开始吆喝,多是短打褐衣的男子,却也不乏头巾包布的女娘忙活其中。
自南朝初立以来,因着战乱人丁不息,太祖登基后颁布诏令,鼓励寡妇再嫁,兴添人丁,世道于女子并不多加缚束。
今日的后街异常沸腾,木制告示板前里三层外三层的围满了人群,热火朝天的议论钻进徽音等人耳中。
“长安令告民:东瓯反叛,卫将军裴彧率两万精兵迎战,破敌五万,大捷!扬我国威,与民同庆,赐民酺五日!”
“这裴彧是何许人?”
“这位来历可不小,乃是当今皇后内侄,太子殿下的表兄,自幼在陛下跟前长大,连几位皇子都没他受宠。”
“他出身如此尊贵,怎的还领兵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