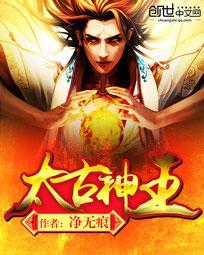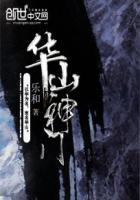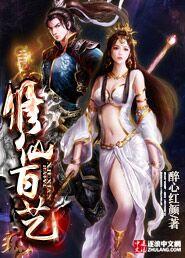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天启大明免费阅读 > 第66章 东林党到底是什么底色(第1页)
第66章 东林党到底是什么底色(第1页)
“左光斗左共之,孙伯雅你服不服?”
孙传庭咽了咽口水,訕笑道:“皇上,你说共之先生,那臣必须服。”
朱由校謔笑地问:“为什么服?”
“皇上,天启元年,共之先生领直隶屯田事,写了《足餉无过屯田,屯田无过水利疏》,当时臣任河南永城知县,在邸报看到这份上疏,歷歷在目,记忆犹新。
共之先生说,北方地区非常特殊,如果不兴建水利,一年之后容易造成耕地荒废,两年之后农民见状就会背井离乡,数年之后这块地就不再適合耕种了,而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容易饿死。
臣当时勘查过永城县各乡镇,验证了共之先生的说法没错。”
孙传庭双眼炯炯有神。
“共之先生提出北方应效仿南方,兴修水利,开荒屯田,引进种植水稻等措施。臣在永城按照共之先生的《三因十四议》,试著行了浚通河流,挖渠和引水,略有小成。”
朱由校背著手,站在窗前,看著夜色。
“左共之的《三因十四议》疏,朕也看过。
一因天时,二因地利,三因人情。
一议浚通河流,二议挖渠,三议引水,四议修坝,五议建闸,六议设坡,七议地势,八议筑塘,九议招徠百姓,十议选人,十一议选將,十二议兵屯,十三议种田赋额,十四议富民可以拜爵。
都是肺腑良策,而且多是从实践考虑的可行之法。”
孙传庭看著朱由校的背影,心里翻腾不已。
皇上不像那些人说的昏庸懦弱,他心里有大明,有苍生黎民。
他机敏睿智、心思縝密,坚毅果敢、当机立断,现在已经显现出一代雄主明君的气质。
现在的大明需要一位气逾霄汉、旋乾转坤的雄主明君,只有这样才有希望。
迟疑了二十余息,孙传庭终於开口。
“皇上,臣恳请赦免左共之杨大洪等六人。”
朱由校猛地转过头来,目光如刀剑一般看著孙传庭。
“你是东林党人?”
孙传庭强撑著答道:“回皇上的话,臣不是东林党人。
在臣看来,东林党人只是一个標识,一个象徵而已。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东林党人,谁也可以说自己不是东林党人。”
朱由校突然笑了笑,“不要紧张,朕只是跟你聊聊。
你说的没错,东林党只是一个標识。
起初东林党只是以东林书院为纽带的江南士子社团。后来在国本之爭中,东林党日渐兴起,名声大噪,於是许多人慕名加入,也有许多人声称自己就是东林党人。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绍徽,向魏忠贤进献了一本《东林点將录》,仿水滸传一百零八將,把朝中大臣编成东林党一百零人。
真是愚蠢到家的蠢货!
他不想著如何瓦解东林党,居然还把意见与己不同的大臣们,统统扣上东林党的帽子,再公布於世。
他是嫌东林党名声还不够响,要把许多其实是中立的大臣和士子们都往东林党那边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