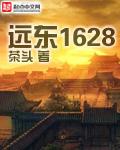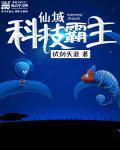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五零二婚夫妻日子忙百度百科 > 刘老师(第1页)
刘老师(第1页)
东头杜家家里,刘翠花的前小姑子杜西看着村里人在疯狂的认字,就有点想去学,奈何她妈不同意。
老太太认为识字耽误给家里人干活,而且女孩子家学了有什么用,她一辈子不认字不也活了一辈子吗?学那东西不当吃不当喝的。
土墙根下,杜西正攥着半截炭头,在青石板上歪歪扭扭地画着"人"字。灶间传来杜老太太的咳嗽声,柴刀在砧板上哒哒的切着菜。
杜西的视线却总往晒谷场飘。那里支着块新刷的黑板,王先生正教女人们写自己的名字,她低头看看自己结满茧子的手心,听见老太太嘟囔:“你姑奶奶裹三寸金莲那会儿,连《女儿经》都请人念,现在倒好,女娃子想飞上天咧!”
杜西突然就觉得“凭什么呀,前大嫂识字,现在的大嫂也识字,为啥到自己这里就不行呢,自己就要学,大大方方的学”。
站起来,也没看她妈一眼,往晒谷场而且。
县城里,街道办没想到扫盲大家会这么热情,光晚上时间不够。
白天大家也要要求学习,于是刘翠花终究把自己下午的时间贡献给了扫盲班上课。
十一月的县城下午已经凉意渐浓了,县城文化站的门前已聚集了二十多个身影。穿工装的汉子攥着铅笔在膝盖上反复划横竖,带孩子的妇女把识字本翻得哗啦响,几个半大小子踮脚张望教室里的黑板——这些白天在菜场、工厂、工地忙碌的居民,此刻都成了扫盲班最积极的学生。
教室角落堆着各家凑来的板凳,黑板上,上节课擦完的痕迹还那么明显,粉笔灰掉了满地。还没到上课时间,王铁匠已经举着写满拼音的烟盒纸追问刘翠花,他媳妇则把孙子的作业本改成了练习册,扉页上郑重其事地印着李秀梅三个描红字。
刘翠花将教材抱在胸前,纸页边缘被翻得微微卷起,她有点紧张了,深吸一口气,凉风钻进鼻腔里,没啥大不了的,自己没在学堂读过书是环境因素,她清了清嗓子,王铁匠突然站起来,粗着嗓子喊了声“刘老师好”!随即教室里顿时响起一片稀稀拉拉的应和,几个孩子还咯咯地笑。
刘翠花努力压下去的心虚,扑面而来顿感到脸颊发烫,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教材的封面,突然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身份——不是厨子。在灶台多年的刘翠花突然意思到这不是以前了,他们的努力终于让所有人过上了好日子。
下边二十多双眼睛注视着刘翠花。她挺直了背,在黑板上写下“人”。
刘翠花上完一节课出来时,卲一平一身警服站在屋檐下,看着刘翠花出来,跑到她跟前问道:“怎么样,还好吧?”
刘翠花感觉到他比自己还紧张,不解道“我上课我都不紧张,你紧张个啥劲呢?”
卲一平看她这样子,只能无奈的说:“你一天没上过学,突然教这么多人,我能不担心吗?”
“担心啥?”
卲一平也说不上来,欺负肯定是不会被欺负,可自己心里就是放下不下。
刘翠花自己虽然当时有点紧张,但自己现在肯定是不能承认的。看他半天也说不上来,就直接说道“瞎担心,你这是不了解我的实力呢还是不了解我的能力”
然后直接定性道“走,回家”
到家才对着卲一平说道:“大家学习这么热情,应该给他们找正规的老师教,不应该但凡认字,就直接教。这样对他们不好”。
卲一平点点头:“暂时的,现在普法跟扫盲各上一天,即便教的有问题也能及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