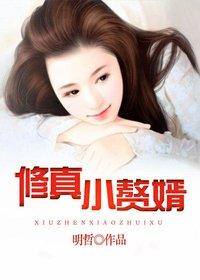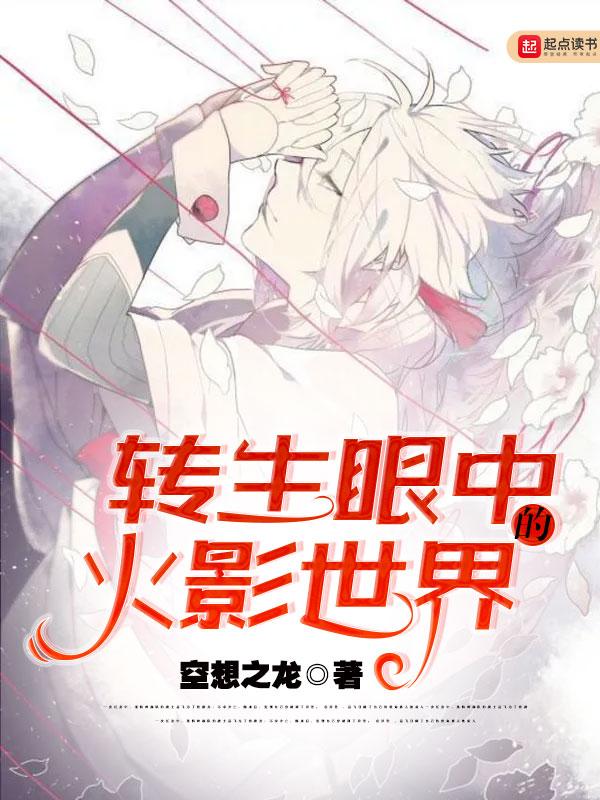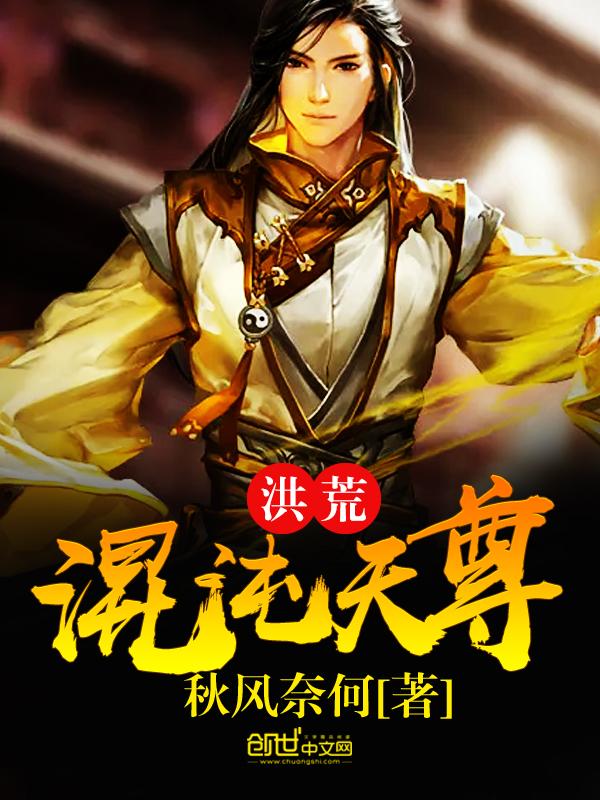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生之我有一间糖水铺子免费阅读 > 三计全失(第1页)
三计全失(第1页)
初冬的汴水早已结了薄冰,漕船破开冰层前行时,船底传来“咯吱咯吱”的轻响,像谁在雪夜里轻轻叩门,又像战场厮杀后残留的兵器碰撞声。萧子良坐在船舱内,案上摊着河南道漕运的卷宗,指尖反复划过“冬运粮草调度”的条目,墨迹都快被磨淡了,却依旧没看出半分破绽。窗外忽然晃过一道浅影,他目光骤然聚焦,看清以后松了一口气,不是奸细,是陈曦。
陈曦两辈子都没坐过漕船,从开船起就没安分过,这会儿正扒着船头的木栏杆,裹着件灰布厚棉袍,领口露出半片月白里衣,风把他额前的碎发吹得贴在脸颊上,鼻尖冻得通红,却像株在寒风里倔强生长的小树苗,眼睛亮得很,正盯着冰面下偶尔游过的鱼群看。
“进来暖暖,外面风大,仔细冻着。”萧子良收回目光,拿起桌上的铜制暖炉,炉身裹着层厚布,还带着余温,递到刚掀帘进来的陈曦面前。陈曦接过暖炉,双手拢在上面,指尖的凉意渐渐散去,他笑着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油纸被体温焐得软了些,打开时飘出淡淡的酥香:“这是今早特意做的沙棘酱酥饼,用上次采的沙棘熬的酱,酸中带甜,你尝尝,能解乏。”
萧子良拿起一块咬了一口,酥皮簌簌落在膝上,酸甜的沙棘酱在舌尖化开,带着几分暖意,竟比宫里御厨做的点心还合心意。他嚼着饼,忽然想起三年前打西域的日子,那时候他领兵在沙漠里,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更别说这样的甜食。“你这手艺,若是再开家点心铺,定能火遍京城,说不定你的‘手艺’还帮我们找线索。”
“怎么可能?”陈曦下意识的反驳,他心想,他只会做糖水点心,查案这种事,哪能帮上忙?可看着萧子良认真的眼神,他还是点了点头,目光落在案上的卷宗上:“殿下,河南道的漕运账目,可有不对劲的地方?”
萧子良指着卷宗上“押运银两”的条目,指尖在“十二万两”和“十万两”之间顿了顿:“你看,这里写着‘河南道冬运漕银十二万两’,可户部收到的只有十万两,差额两万两,他们只说是‘运耗’。但按《大齐律·漕运律》,运耗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十二万两最多只能耗损一千二百两,这两万两的差额,明显不合规矩。”
陈曦凑过去细看,指尖轻轻点在“运耗”二字上,指甲盖都泛白了:“会不会是他们把农税银混在漕银里押运,趁机克扣?就像……就像打仗时有人私藏粮草似的?”他没打过仗,只是从话本里看过。
萧子良眼底闪过一丝赞许,指尖无意识摸了摸手腕上的旧疤,他在三年前打西域时留下的。“你倒机灵。”他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沉了些,“三年前我领兵打西域,在莫贺延碛沙漠里,遇上过类似的事。那时候我们追着西域叛军跑了三天三夜,水喝完了,粮也快断了,只能靠沙漠里的胡麻籽充饥。可负责押运粮草的副将,却私藏了半车干粮,说要‘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结果后来遇上沙尘暴,粮车陷进沙里,那半车干粮全废了,有三个弟兄差点饿死。”
陈曦听得眼睛都直了,忘了吃手里的酥饼:“那后来呢?你们怎么突围的?”
“后来?”萧子良笑了笑,语气轻描淡写,却藏着惊心动魄,“沙尘暴过后,叛军摸上来偷袭,那副将还想带着剩下的干粮跑,被我当场斩了。我们靠着剩下的胡麻籽,还有几个西域俘虏教我们找的沙棘果,硬是撑到了援军来。”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的雪上,“那时候我就想,不管是打仗还是治国,最忌的就是中饱私囊,粮草是士兵的命,税银是百姓的命,谁动了这些,就是跟整个大齐作对。”
陈曦没说话,握紧了手里的暖炉,心里忽然懂了萧子良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查农税贪腐,不是为了自己的功绩,是为了那些像沙漠里的士兵一样,等着救命钱过日子的百姓。“殿下放心,要是用得上我,我一定帮你。”他语气坚定,比刚才点头时认真多了。
萧子良看着他认真的模样,嘴角几不可查地勾了勾:“有这个心就好。等我们到了洛阳县,先从漕运、粮票、农税附册三个方向查,总能找到他们的破绽。”
漕船行至洛阳县码头时,雪又下了起来,细小的雪粒落在青石板上,瞬间融成一滩水渍,像眼泪似的。萧子良带着陈曦和几名亲信下船,洛阳县丞赵大人已带着衙役在码头等候,满脸褶子堆着笑,弯腰时腰间的玉带都快滑到肚子上了:“王爷一路辛苦!下官已备好住处,还请王爷移步歇息,暖锅都炖上了!”
萧子良淡淡点头,目光扫过赵县丞身后的衙役,这一个个衣着整洁,腰间的佩刀擦得发亮,连刀鞘上的铜饰都闪着光,哪像个“清廉”县丞该有的排场?他心里便多了几分警惕。
安顿好住处后,萧子良立刻推进第一个方案:查漕运账目。他派心腹暗卫伪装成新来的漕运账房,那暗卫懂账目,还会说几句河南方言,混进去应该不难。可那心腹去了三日,回来时却是跪着进门的,脸色凝重得像结了冰,递上一本薄薄的账本:“王爷,漕运司的账目分‘明暗两本’,这本是明面上的,与户部存档分毫不差,连小数点后的零头都对得严丝合缝;暗地里的账本锁在漕运使的私人暗柜里,属下趁夜潜入,刚摸到柜锁就触发了铃铛,那铃铛连着外面的守卫房,若非暗卫及时用迷烟放倒巡逻卫兵,属下怕是要被当成窃贼抓起来,连带着暴露身份。”
萧子良翻看着那本“明账”,每页都盖着漕运使的朱红官印,字迹工整得像印上去的,找不到半点错处。“他们连账房的后路都铺好了。”他指尖敲击着桌面,声音冰冷,“漕运司的账房每隔三个月就换一批,都是从外地雇的流民,没根没底的,用完就打发走,没人知道上一批账房的去向,连打听都无从下手。这两万两差额,怕是被他们藏进暗账里,换成了金银珠宝,早通过西域商队运走了。”
第一个方案受挫,萧子良没歇着,隔了两日就推进第二个:追查“粮票布票”的流向。按他的推测,地方官贪腐的税银若不敢直接存银庄,定会换成粮票、布票,再通过商户兑换成物资倒卖——粮食、布料都是刚需,就算查起来,也能说是“正常贸易”。
可暗卫分头查访了洛阳县及周边十余县的粮铺、布铺,回来的消息却让萧子良愈发头疼。“王爷,能兑换‘官票’的铺子都是空壳子!”暗卫统领单膝跪地禀报,膝盖上还沾着雪,“铺子的掌柜是临时雇的老汉,每天就坐在柜台后打瞌睡,只知道‘凭票兑粮’,对幕后东家一无所知;铺子的账目也是简单的流水账,只记着‘某日兑糙米几石’‘某日兑粗布几匹’,没有任何与地方官的往来记录。属下顺着铺子的租金追查,发现产权登记在‘永安商号’名下,可这商号三年前就注销了,注册地在京城,如今早没了踪迹,连当年的经办人都找不到了。”
萧子良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眉头拧成了结,像被冻住的绳子。地方官竟连“洗钱”的路子都想得这么周全,比当年的西域叛军还狡诈!用注销的空壳商号控股粮铺,掌柜只负责兑换,不涉及其余,就算查到铺子,也找不到与官员的直接关联,只能不了了之。“这群人,怕是早把贪腐的路子走熟了,连半分痕迹都不肯留下。”他低声自语,心里的沉郁又添了几分,连窗外的雪景都觉得碍眼。
无奈之下,萧子良只能继续尝试推进第三个方案:借“巡视漕运冬防”之名,查农税附册。按《大齐律·食货律》,州县征收农税后,需编制“农税附册”,记录每户农户的缴纳明细,包括“本色”(粮食)、“折色”(银两)的数额、加耗的比例,这本附册比户部存档的总清册更详实,若是能找到,定能发现加耗超额、折色价虚高的证据。
萧子良带着随从去洛阳县粮仓查看,赵县丞全程陪着,像条尾巴似的,端茶倒水极为“热情”,嘴里不停地念叨:“王爷,这粮仓的粮草都是按冬运标准储备的,每袋糙米都过了秤,一斤不少,绝无短缺!您看这粮袋,都是新缝的,防潮布也铺了三层,保证不会发霉!”
他一边引着萧子良查看粮袋,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可每当萧子良提出要查看“农税附册”,他就立刻转移话题,要么说“附册在县衙存档,需派人去取”,要么说“负责管册的小吏今天请假了”。等萧子良派随从跟着赵县丞的亲信去县衙取册,随从回来时只抱了本泛黄的册子,脸上满是无奈:“王爷,赵县丞说今年的附册还在整理,没装订好,这是去年的旧册。”
萧子良翻开旧册,里面的记录清晰详实,折色价写着“三百文每石”,加耗写着“半成”,都符合《大齐律》的规定,显然是特意准备的“干净”册子,用来应付检查的。他没点破,只是淡淡道:“既如此,明日再来看今年的附册吧。”
夜里,萧子良让暗卫盯着县衙,果然没猜错,三更天的时候,赵县丞的亲信偷偷将一个木匣装上马车,赶车的人还蒙着脸,快马加鞭出了城。暗卫悄悄跟上,看着马车停在城外的乱葬岗,亲信四处张望了半天,才将木匣埋在一棵老槐树下,然后匆匆离去,连脚印都用树枝扫平了。
等亲信走远,暗卫挖出木匣,打开时却傻了眼!里面的农税附册早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几片残缺的纸页,上面的字迹被火烤得发黑,模糊不清,连“洛阳县”三个字都只能辨认出一半,更别说农户的缴纳明细了。
三个方案接连受挫,萧子良坐在临时书房里,看着桌上那几片残缺的纸页,雪光从窗外照进来,映得他脸色愈发沉郁,像结了冰的汴水。地方官的老奸巨猾,远超他的预料:漕运账分明暗两本,堵死了查银钱的路;粮票铺是空壳商号,断了查物资的线;农税附册被烧毁,连最后一点希望都灭了。他们像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所有证据都藏得严严实实,连一丝缝隙都不肯留下。
陈曦端着一碗温好的姜枣浆走进来,姜香混着枣甜飘满了书房,他见萧子良神色凝重,便将碗轻轻放在案上,声音放得柔了些:“殿下,先喝碗姜枣浆暖暖身子,查案急不得,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您要是累了,就歇会儿,我守着,有消息了再叫您。”
萧子良接过碗,温热的姜枣浆滑过喉咙,暖意从胃里散开,却解不了心里的沉郁。他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想起皇帝嘱托的眼神:“子良,这事就交给你了,别让百姓失望”;想起秦老头说“税银多缴”时的无奈——“我这三亩地,平白多掏六百文”;想起沙漠里饿死的弟兄,心里第一次生出无力感。难道真的要这样毫无收获地打道回府,让那些贪腐的官员继续欺压百姓,让弟兄们的血白流吗?
他握紧了手中的碗,指节泛白,连碗沿都快被捏碎了,他看着案上的残页,眉头又拧成了结,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像要将整个洛阳县都埋在雪里,连一丝光亮都透不进来。而他的查案之路,也像这漫天风雪一样,看不到尽头。
难道,真的要打道回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