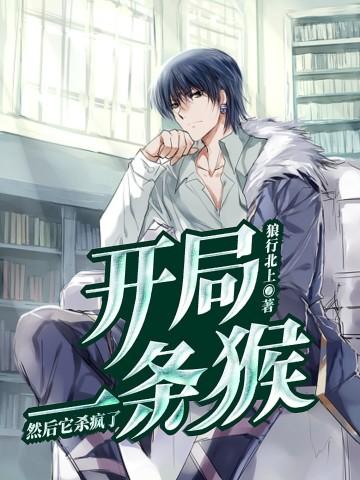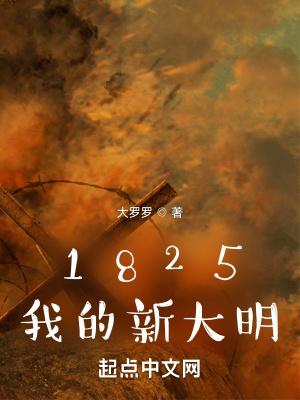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阿苍三个男人的爱情在线观看 > 放逐(第1页)
放逐(第1页)
时间的指针悄然拨回到半年前,北京。
长夜寂寂,静谧笼罩着向耀祖的书房。
这方天地宽敞、典雅,每一处细节都镌琢着主人的品味与岁月。
墙壁上悬挂的名家画作,无声地昭示着主人的气蕴与地位;书架上,除了满满的藏书,几座不同国际影展的奖杯,在幽暗的光线下折射出熠熠光芒,那是他半生荣耀的见证。
向耀祖坐在宽大的书桌后,指尖在键盘上飞快地操作着,屏幕的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庞,眼神专注而深邃。
沙发上,樊灵娟手中捧读一份报纸,目光沉静。
她是向耀祖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无可替代的伙伴,曾经的影坛巨星,如今洗尽铅华,眉宇间添了几分温婉恬适。
报纸上,那条引人瞩目的新闻标题:「名导向耀祖有子承衣钵,畅销小说《哪咤们》筹拍电影」。
这一年,向阳以一本《哪咤们》震动文坛,小说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既剖开了家庭关系中那些温情脉脉的束缚,也吶喊出一个儿子对父权的挣脱与控诉。
那是一本爱情小说,也是书中恋人挣脱父母以爱为名枷锁的故事,引发了无数读者的共鸣。
此刻,小说翻拍成电影的筹拍消息一经公布,便如旋风般席卷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成为热议的焦点。
「哪咤」,这个千百年来「孽子」的代名词,如今堂而皇之地冠于电影之名,彷佛是这对声名赫赫的父子之间,那难以消解的矛盾与纠结,又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脚注,再次成为广大群众雾里看花却总是津津乐道的谈资。
向耀祖终于完成了手头的邮件,点击发送。接着,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那头,是与他合作多年的电影音乐配乐大师,杜天鸣。
杜天鸣接起电话,同一时间,向耀祖刚发给他的邮件,也已经出现在电邮信箱里。
「阳阳那小说洋洋洒洒四十多万字,你不可能有时间细嚼慢咽。」向耀祖的声音透过听筒,语音铿锵,带着跟平日不太一样的殷切,「我整理了一个三千多字的浓缩,你抽空看一眼。这类型的电影,音乐是魂,你帮帮他。」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已经传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放下电话,向耀祖并未停歇,目光依旧锁定在计算机屏幕上,手指熟练地滑动着鼠标,搜寻着网络上的相关信息。
樊灵娟放下手中的报纸,目光投向他。
见他面前那只透明的保温杯中,菊花茶已然见底,便起身,拿起桌角的热水壶,走过去,轻柔地为他续上了热水。
「唉,」樊灵娟轻叹一声,「记者追问他这小说是不是有自传的色彩,他也只是笑,不置可否……这孩子,心里那道坎,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迈过去?」
向耀祖的目光从屏幕上移开,望向窗外的沉沉夜色,声音里有着难得的疲惫与愧意:「人生倏忽,白云苍狗。我自问这一辈子行事磊落,唯独对他母子三人,确实是有亏欠的。」
「血浓于水,哪有解不开的结?日子还长着呢。」樊灵娟的声音温和,带着宁定人心的安抚。
向耀祖看了她一眼,嘴角牵起一抹极淡的微笑:「妳先去忙吧,我再琢磨琢磨,看看还有什么地方能再使上些力气。他的第一部电影,尽量多帮帮他。」
樊灵娟点点头,放下热水壶,转身向门口走去。
门扉轻轻阖上的瞬间,她迅速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指尖划过屏幕,悄无声息地拨通了杜天鸣的电话。
「天鸣,是我,樊姐。」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刚听见向导跟你通电话……提醒你一句,向阳那孩子,若是晓得是他爸求你出马,估计又要炸毛。你就说,是听我提起的……」
相隔几天的午后,秋日的骄阳,明晃晃地泼洒进「闹海电商」的办公室,将每一寸空间都染上了和煦的暖金色。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北京一望无际的繁华。
办公室内的接待区,气氛热烈,议题正酣。
从台北远道而来的音乐大师杜天鸣,此刻正襟危坐,他面前的笔记本计算机屏幕闪烁着幽光。
这是他第一次亲自登门,大马金刀,煞有其事地为向阳筹拍的新电影《哪咤们》举荐配乐作曲的人选。
向阳的发小兼事业上的左膀右臂,彭群山,第一次参与电影项目的规划,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与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