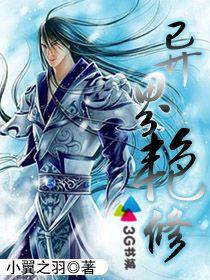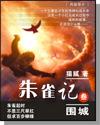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抗战楚云飞机枪阵地左移五米无弹窗 > 第611章 常瑞元 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第5页)
第611章 常瑞元 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第5页)
以及前不久刚和他见过面的延安方面派遣而来的工作代表钟志成。
钟志成也算是楚云飞的老熟人了,自37年开始,他们已经打过了十数次的交道。
至于刘鸿文则是孙桐宣的老熟人。
当年洛阳办事处为了筹集新四军第六支队过冬的服费与孙桐宣打过交道。
孙桐宣更是捐款了足足的五千块。
双方虽然立场不同,却在那次的接触中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基于共同抗日目标的信任。
更何况。
在抗战爆发之前,孙桐宣就和共产党人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
这一点楚云飞也是清楚。
毕竟,能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国军将领数量并不算多。
当孙桐宣从副官的口中得知这三个人联袂而来的消息时。
他知道自己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理由了。
楚云飞这是把所有的牌都摊在了桌面上,他用这种方式清晰地向自己传递了一个信号:我知道你的顾虑,也知道你的人在哪里。
当孙桐宣走出指挥部,第一次主动迎向楚云飞时。
他看到的是一张年轻、沉稳,且带着真诚笑意的脸。
仿佛之前两次的“避而不见”,从未发生过。
“孙总司令。”
楚云飞率先伸出手:“云飞,也算是三顾茅庐终得一见啊。”
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瞬间就化解了现场那略显尴尬的气氛。
孙桐宣敬礼之后,上前握住那只有力的大手。
脸上也露出了苦涩而又释然的笑容:“楚长官,言重了”
没有过多的寒暄。
四人,一同走进了那顶简陋的指挥帐篷。
一场关乎孙桐宣所部乃至整个华北国共关系未来走向的密谈,就此展开。
谈话的内容,楚云飞早已在心中,打好了腹稿。
他开诚布公,没有丝毫的隐瞒和试探。
首先楚云飞肯定了孙桐宣所部在抗战中的功绩。
然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其目前存在的,军纪涣散、装备落后、派系林立等诸多问题。
最后,楚云飞将那份早已经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整编计划和盘托出。
“孙长官。”
楚云飞看着他,语气诚恳:“鉴于贵军目前之现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这支抗日有生力量。”
“我建议,贵军全盘接受‘乙种作战部队’的整编计划。”
“减少重武器的配比规模,强化轻武器火力和机动能力。”
“然后。”
他顿了顿,说出了最关键的安排,“为了保护您,也为了让弟兄们,能有一个安稳的整训环境。
华北联合指挥部将把贵军调往晋西北的综合训练中心,进行为期半年的封闭式整理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