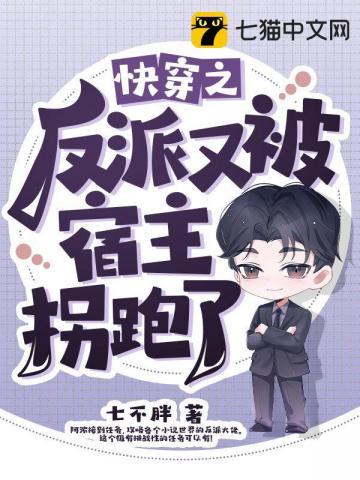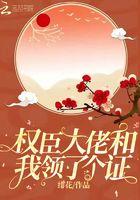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傀儡帝王 > 傀儡(第2页)
傀儡(第2页)
只有户部刘尚书可以在这个时刻理直气壮地面露不虞,因为涉及落籍与土地的如此重大的事项竟无人事先与他商讨过。
若兵户入了边城,那原本归户部管的丁税、田赋、人口,岂不都要分走大半?众臣想着这念头,视线不自觉地朝刘柏亭瞥去。
但他们失望了,作为如今的另一个风暴中心,刘柏亭反而是神色最为放松的一个,连视线都没离开自己的朝笏,就好像这桩事与他无关一样。
其他官员看他不动如山,自然更不肯当出头的椽子。
“孔大人以为呢?”靳羽柯忽然点名。
礼部尚书孔裕圭打了个寒颤,忙起身道:“陛下圣明,此乃社稷之福。”
“崔大人?”他又看向吏部尚书。
崔清沅喉结动了动,最终垂首道:“兹事体大,还请陛下三思。”
“三思?”靳羽柯轻笑一声,“朕倒觉得,这是三思之后的良策。”他抬眼扫过殿内众人,“兵户编审、田亩分配,由户部协办;城防整饬、关都尉任命,由兵部主理。若有疏漏,唯尔等是问。”
周信修与刘柏亭同时出列领旨,本该引起争论的第一件政务就这么平稳地通过了。
就好像所有人都默认他们的皇帝依然在军政事务上拥有绝对的独断专定权,只要他们的旧秩序还在平稳地运行。
只是在那些无声交换着的眼神里,他们确信了,对御案后那人提起警惕的远不止自己。
大殿内跪伏一片,连呼吸都轻得像蚊鸣。靳羽轲望着那片黑压压的头顶,忽然想起周信修私下与他在宫外会面那次,老人将官袍换成一身先生一样的青色长衫,絮絮叨叨说:“陛下如今当雷厉风行,如当年的摄政王一般肃清朝纲。”
他当时只淡淡说了句“各人有各人的命数”,可掩在袍袖下的手,却微微发抖。
他终究不是摄政王,没有那般积威,只能用这般雷霆手段,让这些人明白:他,才是这朝堂真正的主人。
按各部官员原本得到的消息预想,今日的下一项政务应该还是西北之事,且裁撤一事既定,与西獠的议和也该迎来一个终结。
靳羽柯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主动提出要在皇宫内增设罗绮卫一事。
“宫中增设护卫一事,众卿以为如何。”他忽然换了话头,阳光透过大殿前方洞开的四扇正门斜斜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一片阴影。
无人应答,靳羽轲自顾自接着道:“先有钩吻一案,禁卫军分身乏术,朕想着,增设罗绮卫一部,以军中闲职子弟充之,担殿前护卫之责,分禁军之忧。”
话落,台阶上的帝王神色自若,“众卿,可有疑议?”
礼部尚书与吏部尚书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困惑。这罗绮卫来得蹊跷,既不属五军都督府,又不归十二卫管辖,倒像是皇帝私人的卫队。可当他们抬头望向龙椅上的少年时,终究没敢多问——自登基后,这位小皇帝做的事,哪一桩不是先斩后奏?
何况这也算是皇帝家事,他们就不好再多言。方才因兵户一事安静下来的大殿内此时仍浸在一片寂静里,吏部尚书崔清沅想到户部刘柏亭刚才的反应,也干脆当起了缩头乌龟,只惯例以兹事体大为由劝诫皇帝三思而后行。
“陛下……”崔清沅犹豫着开口,“罗绮卫事关城防,当与户部、兵部共商……”
“不必了。”靳羽柯打断他,“朕心里有数。”
崔清沅闭了嘴,额角的汗顺着鬓角滑进衣领。
按身份职责他不得不出言,但是这时候冒头,那滋味可真是叫人难受。
但他这句话还是提醒了靳羽柯,于是他转头看向主管城防的都尉使与禁军统领道:“那便容后再议,待孤与众卿议定一应事项,再颁布旨意。”
其实就是粉饰太平罢了,崔清沅顺从地没有再劝,安心地等议和一事被提出。
然而并没有,接着小皇帝命令六部三公各官员按例述职,等流程走完已是红日当空,就在所有人都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从大殿正前方突然传来两个字:“退朝。”
靳羽轲话落站起身,施施然道,兵部官员留朝共商大计,其余人等若无本启奏则依次退朝。
其他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壮着胆子抬眼一瞥,皇帝冕旒上的玉藻晃出细碎的光,殿外的阳光正好,照得他的龙袍泛着金红的光泽,倒像是裹了层血。
吓得纷纷一抖,不敢再看,更不敢多言。
其实这在靳云当政时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安排,小皇帝登基后也只亲近兵部官员与禁军都尉等亲信。
然而如今竟连议和这样兹事体大之事都不与他们商讨一二,众官员心理素质差一点的险些当场色变,好些的也是面容沉肃,心下不知在想着什么。
待大部分官员退下后,大殿里只剩兵部的几位官员。靳羽柯解下冕旒,揉了揉发涨的太阳穴。紧握的手掌心里,那张夹在兵部尚书奏折里的字条已经被汗水浸透发皱,墨迹晕开,模糊的墨迹里只依稀看得出四个字:
“容后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