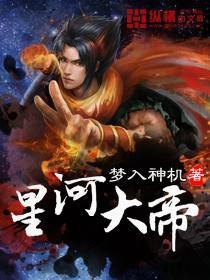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芳华年代完整版 > 第 7 章 士兵安置(第1页)
第 7 章 士兵安置(第1页)
宁政委的来访和那个夜晚的沉思,如同投入湖心的石子,涟漪散去后,湖面复归平静,却似乎比以往更加深邃清澈。刘峰的生活节奏依旧,每日早早来到“北京经济技术咨询中心”,打扫、烧水、看报,处理那些琐碎却维系着生计的“信息业务”。
但他心中那点关于退伍军人的念头,并未熄灭。他开始有意识地在与人交谈时,留意相关的信息。去街道工厂联系边角料时,会状似无意地问一句:“老师傅,咱厂里有没有从部队下来的?干活肯定一把好手。”帮饭馆老板打听便宜羊肉货源时,也会闲聊几句:“现在复员回来的兵安置咋样?我有个远房亲戚正愁呢。”
消息零零散散汇聚过来。情况比他想象的更不易。许多单位宁愿要没经验的学徒工,也不愿意接收身上带伤、可能“麻烦”多的退伍兵,尤其那些农村兵,回到家乡更是缺乏门路。
这日,他骑车去南城一家新开的印刷厂谈一笔小业务——帮他们联系一种价格更实惠的油墨。厂长是个精明的中年男人,一边抱怨着成本上涨,一边对刘峰递上的样品和报价单仔细核算。
谈得差不多了,刘峰收拾东西,像是忽然想起什么,随口问道:“王厂长,我看您这厂子刚起步,业务量上来肯定缺人手吧?尤其是装卸、打包这类力气活,需要可靠的人。”
王厂长叹口气:“可不是嘛!现在招人难,小伙子都心气高,嫌这活累挣钱不多。临时工又不放心,怕把东西弄坏了。”
刘峰沉吟一下,说:“我认识几个去年从南边回来的兵,都是野战部队下来的,吃苦耐劳没得说,组织纪律性也强。就是……可能身上都带点小伤,但不影响干力气活。人品绝对靠得住,您要有意向,我可以帮着问问?”
王厂长愣了一下,打量了刘峰几眼,似乎没想到这个做“信息咨询”的还会揽这活儿。他犹豫着:“退伍兵?好是好…·…就是……听说有的脾气弹,不好管,而且这伤残…···
“都是轻伤,不影响干活。脾气您更放心,部队出来的,令行禁止。”刘峰语气平和却笃定,“您可以先见见人,试用两天,觉得不行,我立马领走,绝不给您添麻烦。”
或许是刘峰之前谈业务时表现出的可靠起了作用,王厂长想了想,最终点了点头:“成!刘经理你介绍的人,我信得过。先叫两个来试试工,按临时工算钱,干得好再说。”
“欸,好嘞!谢谢王厂长!”刘峰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这比他谈成一笔生意更让他感到踏实。
回去后,他立刻通过几条辗转的关系,联系上了两个正在家待业、为工作发愁的退伍兵。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胳膊受过伤阴雨天会酸,一个听力稍微受损,但身体底子都好,眼神里透着对工作的渴望。
刘峰亲自带他们去了印刷厂,跟王厂长见了面。两个小伙子站得笔首,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透着军人的耿首和拘谨。王厂长看了看他们的身板,简单问了问情况,还算满意。
几天后,刘峰特意又去了一趟印刷厂。王厂长一见他,就笑着递过来一根烟:“刘经理,你介绍那俩小子,真不错!干活实在,不惜力,厂里东西收拾得利利索索,比那些磨洋工的强多了!就是话太少,闷头干!”
刘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笑道:“那就好,您用着顺手就行。”
离开印刷厂,傍晚的风带着暖意。虽然这只是解决了两个人的工作,微不足道,但刘峰却觉得脚步格外轻快。他想起前世那些沉默的、眼神荒芜的士兵,至少,他眼前的这两个,眼里重新有了光。
这种成就感,不同于赚到一笔中介费的喜悦,它是一种更深沉的、源于内心深处的慰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刘峰依旧忙碌着他的小生意,时而顺利,时而碰壁。他帮人牵线买到了一批急需的电子元件,也曾在试图联系一单外贸服装尾货时被人骗了少许定金,学到了教训。他像一株坚韧的植物,在市场经济的初春雨露和风沙中,缓慢而扎实地生长着。
他与何小萍的信件依旧定期往来。她的信越来越长,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专业更深的理解和困惑,偶尔也会提及大学生活里的趣事和烦恼,笔触渐渐褪去了最初的生涩,多了几分自信的锋芒。刘峰的回信依旧简短,却总能切中要害,或是几句鼓励,或是一点看似不经意的点拨,却总能让她豁然开朗。
他会在汇款单附言栏里,写上“买双好点的舞鞋”或“添件新衣”,一如既往的不容拒绝。他想象着她收到汇款单时,那微微蹙眉又无奈接受的样子,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
偶尔,在奔波一天之后,深夜独自回到小屋,他会就着台灯,仔细擦拭那台半导体收音机,调频到一些模糊的境外电台,听着里面关于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只言片语,眼神幽深,若有所思。
这个机会,他隐约感觉,或许就在那些不断涌入市场、却尚未被充分重视的“技术”和“人才”之中。那些在国营大厂里被闲置的技术,那些像梁工一样有本事却不得志的人才……如何将这些沉睡的资源与南方蓬勃的需求对接起来?
他铺开信纸,这次不是给何小萍回信,而是开始罗列自己认识的一些技术人员的名字和他们的专长,又在另一边写下南方可能需要的产品和技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