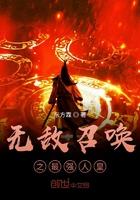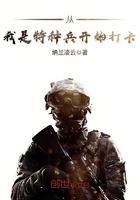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司马师曹髦 > 第64章 雨停刃出宫门将裂(第2页)
第64章 雨停刃出宫门将裂(第2页)
当年曹彪被赐死,宗室株连甚广,这才彻底奠定了司马氏在朝中的绝对权威。
他是魏室血脉最为纯正的象征之一,倘若陛下此刻要为其延续后嗣,甚至将其后人立为储君,那司马氏“代魏”的大义名分,岂不是要动摇根基?
荀勖不敢有丝毫怠慢,甚至来不及详查真伪,便立即备车,亲赴司马昭府邸。
“二公子,大事不妙!”荀勖一入书房,便屏退左右,急声道,“陛下欲续楚王血脉,恐非善兆,此举意在动摇国本!”
司马昭正在擦拭佩剑,青铜剑身映出他冷峻的脸庞。
听闻此言,动作猛然一滞,布巾停在刃口,发出轻微摩擦声,如同蛇鳞刮过石面。
空气仿佛都在瞬间凝固。
他的脑海中轰然炸响,眼前浮现出多年前那个血腥的雨夜——父亲司马懿下令屠戮宗亲,殷红的血水顺着府邸的石阶汩汩流下,汇成一片触目惊心的赤色。
那晚的铁锈味至今仍萦绕鼻端,梦中常闻哀嚎。
曹彪的死,是司马家权势的奠基石,也是司马昭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自幼便被父亲教导“养虎必定遗患”的道理,此刻听闻曹髦竟敢触碰这道逆鳞,胸中压抑多年的暴戾与惊惧瞬间喷涌而出。
“砰!”他一掌拍在案上,剑鞘随之震颤不己,檐角铁马叮当作响,似为这场风暴提前奏响序曲。
“这绝非偶然!必是那小皇帝曹髦勾结朝中残党,图谋复辟!”司马昭双目赤红,如同被激怒的困兽,在房中来回踱步,靴底踏在青砖上发出沉闷回响。
他不再有任何犹豫,当即铺开笔墨,亲自拟就一封废帝密奏,准备派心腹星夜送往兄长司马师的府邸。
“大将军明鉴,曹髦昏聩无道,包藏祸心,当效仿霍光故事,先发制人,废昏立明!”为增加说服力,他又命人伪造了一封“天子私联蜀汉”的书信副本,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作为曹髦谋反的铁证附于奏后。
最后,他更是主动请缨:“弟愿亲率本部兵马,入宫清肃,以保社稷无虞!”
当司马昭的心腹揣着密奏与伪证匆匆离开府邸时,一阵穿堂风忽自廊外卷入,吹得檐铃叮咚作响,烛火剧烈晃动,光影在墙上扭曲成鬼魅形状。
而在这同一阵风里,东府深处,张春华的寝殿纱帘也被轻轻掀起一角——一道纤影悄然退步而出,如同夜露滑落叶尖,不留痕迹。
侍女张美人敛眉垂首,快步走入后院的阴影中。
这位昔日张夫人的贴身侍女,原为张家陪嫁丫鬟,素得老人信任,多年来负责煎药、奉膳,是唯一可自由出入内寝之人。
今晨,她趁着为病中的张春华喂药之时,附在老人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低语:“奴婢亲耳听见二公子叹曰:‘若非兄长久病,何须我独当危局?’语气之中颇有不甘……”
本就因病而心绪不宁的张春华,闻言浑身一颤,枯瘦的手指猛地攥紧锦被,眼中瞬间迸发出骇人的怒火。
她一生偏爱长子司马师,对其寄予厚望,同时又对次子司马昭的野心与手段素来忌惮。
这句话虽未首言背叛,却足以让她解读为“功高震主,意欲取而代之”。
她当即命人封锁内院,严禁消息外传,随即又唤来一名绝对忠心的老仆,沉声嘱咐:“传我口令,明日朝会,府中诸将,一切当以大将军马首是瞻,不得让仲达之子独掌话语权!”
殿宇深处,最后一缕安神熏香在铜炉中燃尽,化作一缕青烟消散。
曹髦亲手将其吹熄,东方天际,一轮红日己然破晓,万丈金光穿透云层,洒满巍峨的宫城。
琉璃瓦反射出刺目光芒,仿佛整座皇城都在燃烧。
他望着这象征着新生与希望的晨光,唇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轻声自语:“刀,不必出鞘,也能割喉。”
洛阳城从沉睡中苏醒,坊市间的炊烟袅袅升起,犬吠鸡鸣交织成市井的呼吸。
宫城的重重殿门在吱呀声中缓缓开启,铜环撞击的余音久久回荡。
文武百官各自整肃衣冠,从府邸出发,怀着不同的心思,沿着相同的道路,汇向那座决定帝国命运的权力中枢。
有人袖中藏刃,有人怀揣密诏,有人一心匡扶,有人只求自保。
一切看起来,都与往日并无二致,然而空气中弥漫的,却是一股山雨欲来前的沉闷与压抑——那是铁锈般的腥气,是阴谋蒸腾的气息,是历史转折点上最沉默的咆哮。
一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风暴,正在太极殿的金顶之下,悄然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