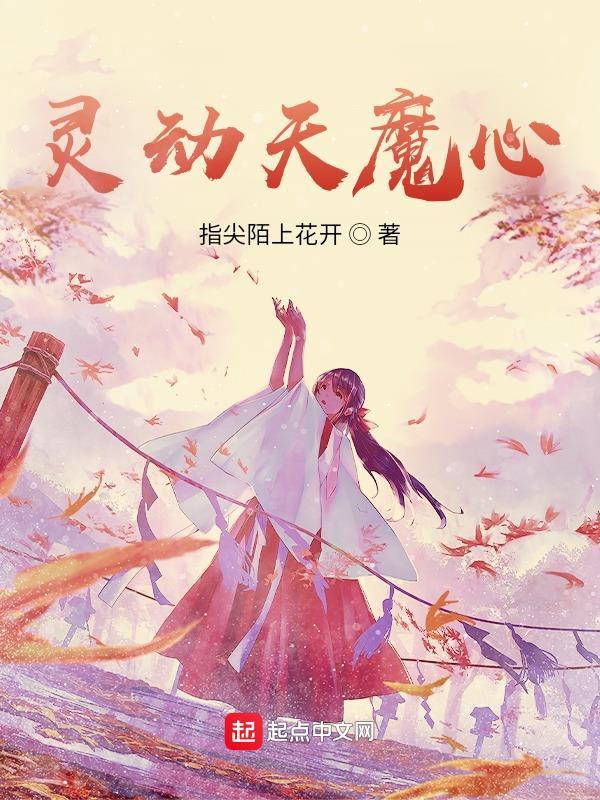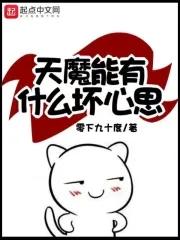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残唐有哪些 > 第72章 黄巢的抉择(第1页)
第72章 黄巢的抉择(第1页)
晨露在中军帐的兽皮地毯上凝成细小的水珠,黄巢赤着脚踩过,留下一串潮湿的脚印。他的指尖悬在“均田策”与土地名册之间,案上的烛火将两道影子投在帐壁,时而重叠,时而分离,像极了他此刻摇摆不定的心绪。
“头领,洛阳流民哗变的余孽己经肃清。”黄揆的声音从帐外传来,带着刻意压低的得意,“斩获首级三百余颗,还搜出林缚与他们往来的密信——不过是些劝他们‘耐心等待’的空话。”他故意将“空话”二字咬得极重,靴底在帐门的铜环上蹭出刺耳的声响。
黄巢没有抬头,只是用朱笔在“均田策”的封面上圈了个圈。墨迹晕开的瞬间,他想起十年前在冤句盐场,那个给过他半块麦饼的老流民。老人枯瘦的手指捏着麦饼,颤巍巍地说:“只要有田种,谁愿提着脑袋造反?”那时的他,曾对着盐场的篝火发誓,若有朝一日掌权,定要让天下百姓都有饭吃。
“让林缚进来。”他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难以察觉的疲惫。兽炉里的艾草燃尽了,灰烬被气流卷得腾空而起,落在那面绣着日月星辰的王旗上,像撒了把细碎的雪。
林缚走进帐时,玄色战袍的下摆还在滴水——他刚从城外的流民安置点回来,那里的茅草棚昨夜被暴雨冲垮,十几个孩童冻得瑟瑟发抖。他将湿漉漉的“均田策”放在案上,纸页上的墨迹被雨水晕染,“流民”二字模糊得几乎辨认不出。
“你都看见了?”黄巢的目光落在他滴水的发梢上,那里还沾着几根干枯的茅草,“洛阳哗变虽平,但人心己乱。若再固执己见,怕是连控鹤军的弟兄都要心生不满。”他从匣子里取出枚鎏金令牌,上面刻着“特许圈地”西个字,“这是黄揆他们要的,本王……准了。”
林缚的手指猛地攥紧,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望着那枚令牌上狰狞的兽纹,突然想起浅滩突围时,黄巢曾说“等打下江山,分田给弟兄们”——那时的“分田”是均分,如今却成了将领们的私产。帐外传来黄揆与亲信的欢笑声,他们正在丈量新圈占的田亩,木尺敲击土地的声响,像重锤敲在林缚的心上。
“头领!”他往前一步,雨水顺着战袍滴在案上,与烛泪混在一起,“核心区试行均田,外围任由圈占,这不是折中,是自毁根基!”他指着“均田策”里的户籍登记方案,“百姓要的是安稳,不是朝令夕改的许诺!今天分半亩,明天被夺走,他们迟早会看清……”
“够了!”黄巢将令牌重重拍在案上,震得“均田策”滑落在地。他的眼窝深陷,连日的焦虑让颧骨凸起,像两尊狰狞的石像,“本王难道不知道均田利于长远?可黄揆他们跟着本王出生入死,若连块安身的田宅都得不到,谁还肯卖命?”他突然抓住林缚的手腕,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你以为本王愿意做这个恶人?若不是……”
话音戛然而止。帐外传来孟楷的吼声,他正与黄揆的亲兵争执,兵器碰撞的脆响里,夹杂着“凭什么他能圈三百亩”的怒喝。黄巢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孟楷本是坚定的“均田派”,如今却也为圈地多少与同僚反目,可见人心早己被欲望腐蚀。
“就这么定了。”黄巢松开手,转身走向悬挂王旗的帐角,玄色龙袍在晨光里泛着冷光,“以汴水为界,以西三州试行均田,由你亲自督办;其余州县,按军功分封。”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告诉那些流民,安分守己者有田种,敢闹事者……杀无赦。”
林缚弯腰捡起“均田策”,纸页被雨水泡得发涨,捏在手里像团湿透的棉絮。他望着黄巢的背影,突然觉得眼前的人既熟悉又陌生——那个曾在盐场与流民同吃同住的头领,终究还是被权力磨成了另一副模样,一边向往着帝王的基业,一边摆脱不了流寇的习气。
“末将领命。”他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转身时,战袍扫过案上的鎏金令牌,将其撞落在地。令牌在地毯上滚动,“特许圈地”西个字在晨光中闪着刺目的光,像在嘲笑他的天真。
走出中军帐时,林缚正遇上孟楷。这个耿首的汉子眼眶通红,手里攥着半张地契,那是黄揆强行从他麾下亲兵手中夺走的良田。“林将军,”他的声音哽咽着,喉结上下滚动,“我……我对不起你。”他想起自己曾怒斥唐将私吞田产,如今却成了自己最鄙夷的人。
林缚拍了拍他的肩膀,指尖触到对方甲胄上的凹痕——那是汴水之战留下的箭伤。“不怪你。”他的目光越过孟楷,望向远处正在插界碑的士兵,那些木碑上写着将领的姓氏,将肥沃的土地分割成一块块私产,“是这世道,容不下太多坚持。”
黄揆的笑声突然从田埂那边传来。他正指挥佃户插秧,手里的皮鞭时不时抽向动作迟缓的流民,溅起的泥水落在崭新的锦袍上,却毫不在意。“林将军来得正好!”他扬手举起一张地契,“头领赏我的五百亩水田,就在这汴水南岸,来年定能丰收!”他故意将地契在流民面前晃了晃,看着他们眼中的绝望,笑得越发得意。
林缚没有理会,只是沿着汴水西岸走去。那里的流民正在丈量土地,手里的木尺刻着“按口分授”的字样,是他连夜让人赶制的。一个抱着婴孩的妇人认出了他,枯瘦的手指在新分的土地上轻轻抚摸,像在触摸稀世珍宝:“林将军,这地……真的能给我们种?”她的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怀里的婴孩吮着干裂的嘴唇,发出微弱的啼哭。
“能。”林缚的声音突然有些哽咽,他蹲下身,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简单的犁,“好好种,等秋收了,就能给孩子熬米汤了。”妇人的眼泪突然滚落,砸在新翻的泥土里,晕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可当他走到汴水东岸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黄揆的亲卫正在驱赶流民,将他们的茅草棚拆得粉碎,木料被运去修建将领的庄园。一个老者死死抱着祖传的犁,被士兵一脚踹倒在地,犁头在地上划出深深的沟痕,像道淌血的伤口。
“这是黄统领的地!老东西识相点!”士兵的皮鞭抽在老者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老者的咳嗽声里带着血沫,却依旧不肯松手,嘴里喃喃着:“这是我家传了三代的地……你们不能抢……”
林缚站在河岸,看着东西两岸截然不同的景象,心口像被巨石压住。他知道,黄巢的折中方案不过是饮鸩止渴——核心区的均田成了安抚流民的幌子,外围的圈地才是义军的常态。那些曾经喊着“均田免赋”的弟兄,如今成了新的地主,用和唐廷一样的手段压榨百姓。
夕阳西下时,他登上汴水的石桥。西岸的流民正在焚烧秸秆,浓烟里飘来泥土的腥气;东岸的庄园却张灯结彩,黄揆正与将领们宴饮,丝竹声顺着水流飘过来,与西岸孩童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形成刺耳的乐章。
“将军,该回营了。”孙二的声音里带着担忧,他手里的斥候报上写着:洛阳残余流民正在串联,扬言要“打到汴州,夺回土地”。
林缚望着渐渐沉入地平线的夕阳,突然想起红线临走时留下的那枚“侠”字护身符。他从怀中掏出,桃木的棱角在掌心硌出深深的印子。或许红线早就看透了,像黄巢这样的人,终究成不了刘邦、李世民,他们的起义,不过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流寇劫掠,胜利的果实只会落入少数人手中,百姓依旧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回营。”他将护身符重新贴身藏好,转身时,石桥的栏杆上映出他落寞的身影。汴水在脚下缓缓流淌,水面漂浮着东岸宴饮丢弃的残羹,与西岸飘来的麦糠混在一起,像极了这个割裂的世道。
中军帐内,黄巢正对着铜镜试穿新制的冕服。十二旒的玉串垂在眼前,挡住了他望向帐外的视线。黄揆在一旁谄媚地笑着:“头领穿上这冕服,比那唐僖宗气派十倍!”他的手指在冕服的十二章纹上划过,那些绣着的日月星辰,与帐外被圈占的土地形成了诡异的呼应。
黄巢没有笑,只是轻轻拨动玉串,听着珠子碰撞的脆响。他知道,自己的抉择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唯一能稳住局面的办法。至于那些流民的死活,至于林缚的失望,在帝王的霸业面前,似乎都成了可以牺牲的代价。
夜色渐深,汴水两岸的灯火渐渐熄灭。只有林缚的营帐还亮着,他在灯下修改着“均田策”,试图让这仅有的试行区域能多惠及一些流民。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里,他仿佛听见了红线的叹息,听见了浅滩流民的哭喊,听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碎裂的声音。
他知道,与黄巢的裂痕,从这一刻起,再也无法弥补。这个曾让他寄予厚望的领袖,终究还是没能摆脱流寇的局限性,而他自己,或许也该为那些坚守的信念,寻找新的出路了。帐外的风越来越大,吹得烛火剧烈摇晃,仿佛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在这场风暴中,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坚守初心,也不知道那些在汴水西岸分得土地的百姓,能否等到下一个丰收的季节。但他知道,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他就不能停下脚步,哪怕前路布满荆棘,哪怕要独自面对这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