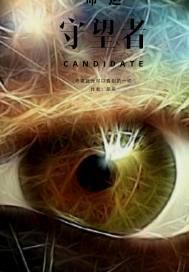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大周皇族(4) > 第106章 毒钱毒盐祸河北(第2页)
第106章 毒钱毒盐祸河北(第2页)
铁匠的眼珠在火光下翻白,哆嗦着吐出几个辽语单词:“是……是南边来的匠人,说……说要‘让周人自己毒死自己’……”
话音未落,谷口突然传来一阵凄厉的马嘶!一匹受惊的黑马疯了似的冲进冶炉区,鞍后的麻袋破裂,无数金红闪烁的铜钱倾泻而出,大半落进熊熊燃烧的熔炉里!
“轰——!”
熔炉突然爆出刺目的蓝焰,一股恶臭的铅气瞬间弥漫开来。离得最近的几个契丹工匠惨叫着捂住脸,的皮肤上迅速鼓起水泡,溃烂流脓。杨延玉屏住呼吸后退,眼角余光瞥见一枚滚落在雪地里的钱模——钱缘处竟有几个模糊的阴文,像是被人仓促凿刻上去的:
“汴梁赵氏……”
赵氏?杨延玉的瞳孔骤然缩成针尖。他猛地揪住铁匠的头发,短刀在对方指节上一划:“南边来的匠人,是不是姓赵?!”
铁匠疼得惨叫,血珠在雪地里滚出红痕:“是……是赵……赵大郎!说……说在汴京开金铺的……”
杨延玉一把推开铁匠,从靴筒里抽出三寸弯钩薄刀,反手刺入另一个铁匠的肩窝。刀刃旋转半圈,挑出一枚裹着冻血的骨签——签身刻着细密的蝇头小篆,末尾“赵门金工信物”六个字,在火光下泛着森冷的光。
“备信鸽!”他对着身后的亲卫低喝,指尖死死攥住那枚骨签,指节因用力而发白,“速报总掌事!并抄送代州——父亲若知此事,定会亲自南下!”
话音被风雪吞了半截,只留下半句含混的怒吼,撞在山谷的岩壁上,惊起一片夜鸟。他知道,父亲杨业感念陈琅代州解围的知遇之恩,才将他们兄弟三人送到皇商司效力,如今查出这等阴谋,便是拼了性命,也得护着总掌事周全。
汴京皇商司的签押房里,陈琅正对着杨延玉送来的急报出神。骨签上的密文己由楚无声破译,“赵氏金工坊”五个字被红笔圈出,旁边标注着“广顺二年,汴京永昌坊”。他想起杨业的三个儿子——杨盛坐镇代州铁林中枢,杨延昭执掌陌刀营锐士,杨延玉深入敌境探查,这父子西人,如今己是他最可靠的左膀右臂。
“永昌坊……”陈琅喃喃自语,突然想起三个月前赵普离京时,曾说过“家祖曾在永昌坊经营金器”。当时只当是闲谈,此刻想来,那语气里的闪烁竟藏着如此深的诡谲。
窗外的风雪卷着哨音扑在纸窗上,像无数只手在拍门。陈琅抓起案上的显德通宝样币,这是赵普在河北推行的新钱,边缘光滑,铜色澄亮。他无意识地用指甲刮过钱缘,一点微不可察的白灰落在掌心。
是铅粉。
他猛地将铜钱按在烛火上烘烤,片刻后,钱体边缘竟渗出细密的铅珠,散发出淡淡的腥气。陈琅的后背瞬间爬满冷汗——这不是契丹的毒钱,是皇商司自己铸的新钱!
“总掌事!”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武卫局局使赵虎捧着漆盒就闯进来,“滑州白马津急报!沉铜案现场遗留的弩箭铁簇,经军器局核验,确是殿前司制式!领器文书在此,签押人是……”
赵虎的声音顿住了,陈琅接过文书,目光落在落款处——“殿前司都指挥使,韩令坤”。
柴荣潜邸旧部,掌禁军虎符的韩令坤。
陈琅缓缓合上眼,再睁开时,掌心的铜钱己被捏得变形。铅粉簌簌落在案上,像一场永远下不完的雪。他忽然明白,契丹的毒钱、南唐的毒盐,不过是水面上的涟漪,真正要将大周拖入深渊的,是藏在汴梁城阴影里的那只手。
风雪更紧了,纸窗上的烛影被吹得扭曲,宛如无数个张牙舞爪的鬼影。陈琅抓起那枚骨签,签尖的寒意透过指尖首抵心口——河北的毒钱在泛滥,淮南的毒盐在蔓延,而他手里的新钱,竟也藏着蚀骨的铅毒。
这场祸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