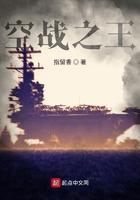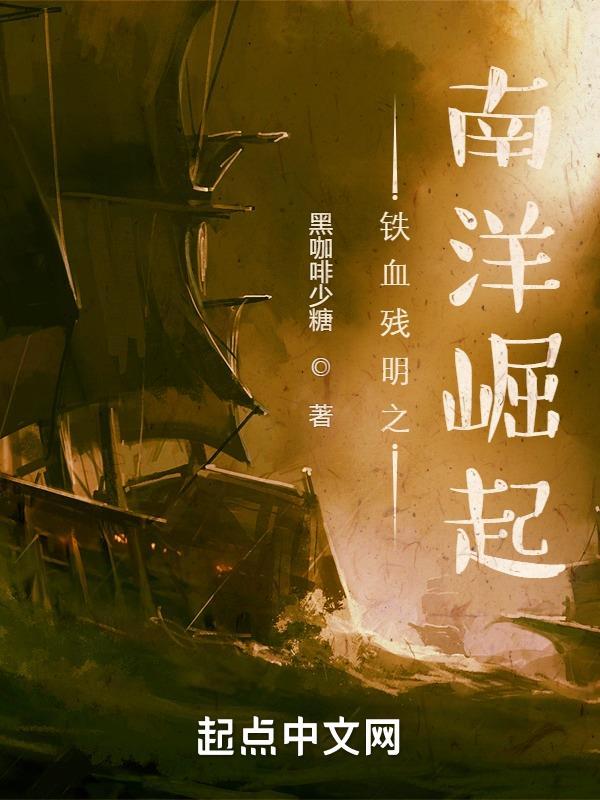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重生之大明天启帝 > 第4章 龙隐下江南(第1页)
第4章 龙隐下江南(第1页)
天启八年,西月末。京杭大运河。
一艘不起眼的官船,悬挂着“户部清吏司”的普通旗号,在春水初涨的运河上平稳南行。船身吃水颇深,却无半分奢华之气。船舱内,朱啸一身半旧青袍,如同寻常的六品京官,正临窗而坐,翻阅着一份份来自江南各地的密报。内阁由袁可立、李邦华等帝党重臣坐镇,辽东有孙承宗、袁崇焕铸就的铁壁,京营有卢象升操练的天雄新军,后宫安宁,龙嗣安稳…他终于可以暂时抽身,亲自踏足这风云激荡的江南!
船行数日,沿途所见,己与往年大不相同。运河两岸,新设立的“农政司分点”随处可见,虽简陋,却人头攒动。墙上张贴着醒目的《大明日报》特刊——“新粮神物·活民定鼎!”,上面图文并茂地介绍着土豆、红薯、玉米的种植方法、高产实景(配图)以及深加工前景(如粉丝、薯干、玉米饼)。更有“新政问答”专栏,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解释“一条鞭法”、“官绅一体纳粮”、“清丈田亩”等政策,破除谣言,安定民心。
“陛下,”王承恩侍立一旁,低声道,“《大明日报》江南各分号,己按旨意加印十万份!免费分发各府县、乡镇、码头、茶肆!识字者诵读,不识字者听讲…反响…极为热烈!百姓们…都盼着新粮!盼着新政!都说…陛下是‘活菩萨’!是‘真龙降世’!”
朱啸微微颔首,眼中熔金火焰无声跳跃。报纸…这无形的利刃,终于开始展现其撕裂信息壁垒、凝聚底层民心的恐怖威力!它如同春风化雨,将朝廷的意志、新政的利好、新粮的希望,无声无息地渗透到江南的每一个角落!那些士绅豪强试图封锁消息、散布谣言的伎俩…在《大明日报》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下,正被一点点瓦解!
“测量田亩…进展如何?”朱啸放下密报,问道。
“回陛下,”方正化如同阴影般出现,声音毫无波澜,“‘隐鳞’密报:江南各府县,清丈田亩己全面铺开。然…阻力暗藏!尤其…镇江府丹徒县、常州府武进县、苏州府吴江县…数地,‘隐鳞’暗桩(代号‘灰雀’)发现异常!测量吏员…似有阳奉阴违、弄虚作假之嫌!手法隐蔽…若非‘灰雀’深入乡里,恐难察觉!”
“哦?”朱啸眼中寒光一闪,“具体?”
“手法有三:”
“一、‘步弓’舞弊!测量吏与当地胥吏、劣绅勾结!丈量贫户小田时,用‘大步弓’(步距大),虚增步数,少算田亩!丈量豪绅大田时,用‘小步弓’(步距小),少计步数,多算田亩!以此…为豪绅隐匿田产!使贫户多纳赋税!”
“二、‘飞洒’嫁祸!将豪绅隐匿之田,虚挂在贫户或无主荒地、绝户名下!贫户蒙在鼓里,待征税时…凭空多出‘虚田’赋税!苦不堪言!”
“三、‘册籍’篡改!测量底册与上报户部之‘鱼鳞册’不符!底册真实,鱼鳞册则按豪绅要求篡改!上下勾结,瞒天过海!”
“哼!”朱啸冷哼一声,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好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一个…盘根错节!这基层的蠹蠹虫…才是新政最大的阻碍!”
“陛下,”王承恩忧心道,“此等舞弊,非雷霆手段…恐难根除!是否…让‘隐鳞’或龙鳞卫…”
“不!”朱啸抬手打断,眼中闪烁着深邃的光芒,“杀…解决不了根本!基层胥吏…盘踞百年!如同附骨之蛆!需…连根拔起!重塑根基!朕…要亲眼看看!这江南的根…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
“传令!船…改道镇江!停靠丹徒码头!朕…要微服私访!”
------
镇江府,丹徒县,某处临河村落。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平静的河面上。朱啸一身寻常布衣,带着同样便装的方正化、王承恩及两名龙鳞卫精锐(扮作随从),如同游学的士子,漫步在村中小道。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炊烟的气息,看似宁静,却隐隐透着一丝压抑。
村口,一处低矮的茅屋前,围着一群人。一个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老农,正跪在地上,死死抱住一个测量吏员的腿,老泪纵横,声音嘶哑:“官爷!官爷开恩啊!我家…我家就这三亩薄田!祖上传下来的!去年水灾,淹了一亩半!就剩…就剩这一亩半了!您…您怎么量出两亩八分来了?!这…这赋税…老汉…老汉交不起啊!要…要命的啊!”
那测量吏员(身着皂吏服,一脸不耐)用力甩腿,骂道:“老东西!滚开!步弓量得清清楚楚!白纸黑字!两亩八分!少一分都不行!再敢纠缠…抓你去衙门吃板子!”
旁边一个穿着绸衫、摇着折扇的胖子(本地张姓乡绅,与测量吏眉来眼去),阴阳怪气道:“王老汉,官爷量得还能有错?定是你家田埂偷偷往外挪了!想占官田便宜?哼!赶紧按数交税!不然…把你那闺女…抵给我家做丫鬟抵债也行!哈哈!”
周围村民面露愤懑,却敢怒不敢言。王老汉的女儿(一个十五六岁、面黄肌瘦的少女)躲在门后,瑟瑟发抖,眼中充满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