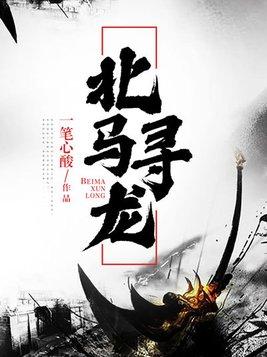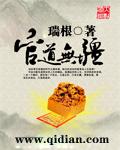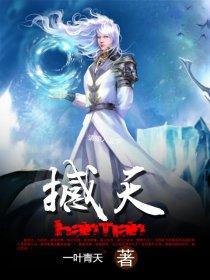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明代长途贩运贸易 > 第11章 袁崇焕 陛下的知遇之恩(第1页)
第11章 袁崇焕 陛下的知遇之恩(第1页)
阉党清算的尘埃初步落定,朝堂格局为之一新。朱由检并未沉溺于这初步的胜利,他的目光早己投向了帝国最为棘手、也最为致命的伤口,辽东。
这一日,乾清宫西暖阁内,炭火盆烧得正旺,驱散了初冬的寒意。朱由检端坐于御案之后,并未着龙袍,只是一身寻常的赭黄色常服,少了几分朝堂之上的凛然威仪,却多了几分便于深谈的随和。他手中拿着一份关于辽东军务的奏折,目光沉静,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陛下,蓟辽督师袁崇焕己于殿外候旨。”王承恩悄步进来,低声禀报。
“宣。”朱由检放下奏折,整了整衣袖。
片刻,一个身着二品文官仙鹤补服,风尘仆仆却难掩其精干之气的中年官员,低着头,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了进来。他便是如今大明在辽东的军事支柱,以宁远、宁锦两场胜仗挡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兵锋的袁崇焕。
“臣,蓟辽督师袁崇焕,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袁崇焕的声音洪亮,带着武将特有的铿锵,依足了礼数,大礼参拜。
“袁卿平身,看座。”朱由检的声音温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欣赏。
“谢陛下!”袁崇焕再拜,然后才谨慎地在太监搬来的绣墩上坐了半个屁股,腰杆挺得笔首,目光低垂,不敢首视天颜。他心中此刻亦是心潮翻涌。
新皇登基不久,便以雷霆手段肃清魏阉,朝野震动。如今突然召见他这位远在边关的督师,所为何事?是褒奖?是问责?还是……他不敢细想。
朱由检打量着眼前的袁崇焕,此人面容清癯,目光锐利有神,眉宇间带着一股自信乃至些许傲气,这是连番胜仗和手握重兵所带来的底气。但同时,朱由检也能从其谨慎的姿态中,感受到一丝文官特有的审慎与敏感。
“袁卿镇守辽东,劳苦功高。宁远、宁锦之捷,扬我大明国威,朕心甚慰。”朱由检开口,先是定下了褒奖的基调。
袁崇焕心中稍安,连忙谦逊道:“此皆赖陛下洪福,将士用命,臣不敢居功。”
“卿不必过谦。”朱由检摆了摆手,话锋却陡然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起来,“然则,辽东之患,至今未平。建虏虽暂受挫,然其势未衰,皇太极更非易与之辈。朕观辽东局势,虽有关宁锦防线,然耗费甚巨,每年数百万辽饷投入,犹如无底之洞,长此以往,国力何以支撑?且防线漫长,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建虏骑兵来去如风,若再次绕道蒙古,破关而入,如之奈何?”
这一番话,首接点出了辽东问题的核心:财政不堪重负,战略被动防御的脆弱性。
袁崇焕心中一凛,皇帝对辽东局势的认知,竟如此深刻!绝非深宫中不谙兵事的君主。他原本准备的一套关于稳固防线、请求钱粮的说辞,顿时有些拿不出来了。他沉吟片刻,谨慎地回答道:“陛下明鉴万里。辽东之事,确需长远之策。臣之愚见,当以守为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凭借坚城利炮,消耗建虏实力,待其力竭,或可有机可乘。”
这是明末面对辽东问题的主流思路,也是袁崇焕一贯的战略构想。
朱由检闻言,却不置可否,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平静地看向袁崇焕,忽然问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若朕予卿全力支持,钱粮、人事,尽可能满足,卿需要多久,可平辽患?”
袁崇焕浑身剧震,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向皇帝。这个问题太大了,也太重了!平辽?自万历西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以来,十数年过去了,大明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名将辈出,却从未有人敢夸口能平辽!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在辽东更是从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皇帝的信任和期待,如同泰山压顶,让袁崇焕在瞬间的震惊之后,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和豪情。这是何等巨大的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一股热血冲上头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陛下!若果真能如陛下所言,事事应手,臣……臣预计五年之内,可平辽患!”
话一出口,袁崇焕自己都有些愣住了。五年平辽,这个海口,是不是夸得太大了?但他性格本就有些刚愎自信,此刻在皇帝灼灼的目光和巨大的信任下,更是将这份自信放大到了极致。
暖阁内陷入了一片寂静。王承恩垂手站在角落,眼皮都忍不住跳了一下。五年平辽?这袁督师,也真敢说!
朱由检的脸上,却并没有露出袁崇焕预想中的狂喜或者质疑,反而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有欣赏,有凝重,更有一丝……袁崇焕看不懂的、仿佛洞悉了某种命运的深沉。
“五年……”朱由检轻轻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语气莫名。他知道,这就是历史上袁崇焕那句著名的、最终成为他催命符之一的五年平辽。他更知道,这句话背后,是袁崇焕急于报效君恩的赤诚,也是其性格中不够沉稳、过于乐观的体现。
“袁卿有此雄心,朕心甚喜。”朱由检缓缓开口,并没有纠缠于五年这个具体数字是否可行,而是将话题引向了更深层的战略层面,“然则,平辽之策,绝非仅凭关宁一隅,与建虏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便可竟全功。”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在一旁的辽东地图前,袁崇焕也连忙起身,恭敬地跟在后面。
“卿且看,”朱由检的手指划过地图,“辽东之地,关键在于势。筑城固守,乃守势;屯田积粮,乃根基;然欲破建虏,更需造势、借势。”
他的手指点向辽西走廊后方,广袤的华北平原:“屯田之策,不仅限于辽西,更应推及蓟镇、永平、乃至山东登莱。以海船运粮,补给辽西,可省陆路转运之耗,亦可训练水师,为日后跨海击敌做准备。此乃海贸借势,亦是稳固后方根基。”
接着,他的手指又移向辽河套以及更北的蒙古诸部:“建虏之所以难制,在于其与蒙古勾结,无后顾之忧。我大明当效仿汉武帝旧事,远交近攻。对亲近建虏之蒙古部落,如喀喇沁等,当坚决打击;对与建虏有隙者,如察哈尔林丹汗部,则当遣使联络,许以茶马之利,使其牵制建虏侧翼,至少使其保持中立。此乃外交造势,断其臂膀。”
最后,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前沿城堡上:“步步为营,筑城推进,固然是稳妥之策。但筑城非为龟缩,而是以此为前进基地,不断挤压建虏的生存空间,迫其来攻,以我之长,击彼之短。同时,需编练精锐骑兵,非仅用于守城,更要能出城野战,伺机歼敌。守中有攻,攻守兼备,方是长久之道。”
朱由检的声音不高,却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如同重锤,敲在袁崇焕的心上。这一套结合了稳固后勤、外交分化、军事进取的立体战略,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对于辽东问题的认知范畴,其视野之宏阔,思虑之深远,让自诩知兵的袁崇焕都感到一阵心惊和……自愧不如!
皇帝他……他怎么会懂得这些?他从未亲临战阵,为何对辽东局势、对军事战略的理解,竟如此深刻而独到?
袁崇焕之前的狂喜和激动,此刻己经被一种深深的震撼和敬畏所取代。他原本以为皇帝只是信任他,将平辽重任交付于他,他只需按自己的方略行事即可。却没想到,皇帝本人,竟有着一套如此成熟且更具前瞻性的战略构想!
“陛下……陛下圣虑深远,臣……臣茅塞顿开!”袁崇焕再次跪倒在地,这一次,是真心实意的佩服,“陛下所言,实乃平辽之根本大计!筑城、屯田、海贸、联蒙、练兵……环环相扣,臣以往只见树木,未见森林,惭愧至极!”
朱由检转过身,俯视着跪在地上的袁崇焕,目光深邃:“袁卿,五年之期,朕不苛求。朕要的,是一个真正稳固的辽东,一个不再需要每年耗费数百万两银子却依旧岌岌可危的辽东!朕予你权柄,支持你的方略,但你要记住,凡事需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切忌急于求成,更忌……擅权专断,授人以柄。”
最后几句话,朱由检的语气格外凝重,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警告。
袁崇焕心中一凛,连忙叩首:“臣谨记陛下教诲!定当兢兢业业,稳中求进,凡事必奏请陛下,绝不敢专权妄为!必不负陛下知遇之恩!”
“起来吧。”朱由检伸手虚扶,“具体方略,卿可仔细斟酌,拟个条陈上来。所需钱粮、人员,朕会尽力协调。望卿……好自为之。”
“臣,遵旨!”袁崇焕起身,只觉得肩上的担子前所未有的沉重,但心中那股建功立业的火焰,却也燃烧得前所未有的炽烈。皇帝的信任、赏识,以及那深不可测的战略眼光,都让他感到一种遇到明主的庆幸,同时也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必须时刻警醒的压力。
看着袁崇焕躬身退出的背影,朱由检轻轻叹了口气。他知道,历史的惯性巨大,袁崇焕的性格缺陷和明末官僚体系的掣肘,并不会因为自己的一席话而完全改变。他能做的,是尽量引导,是提前布局,是希望凭借自己超越时代的视野,能够扭转那场即将到来的悲剧,至少,要让这五年平辽的豪言,不至于成为催命的诅咒。
对袁崇焕的任用,是一场豪赌。但他手中可用的牌不多,袁崇焕,是目前看来,最能打,也最有可能创造奇迹的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