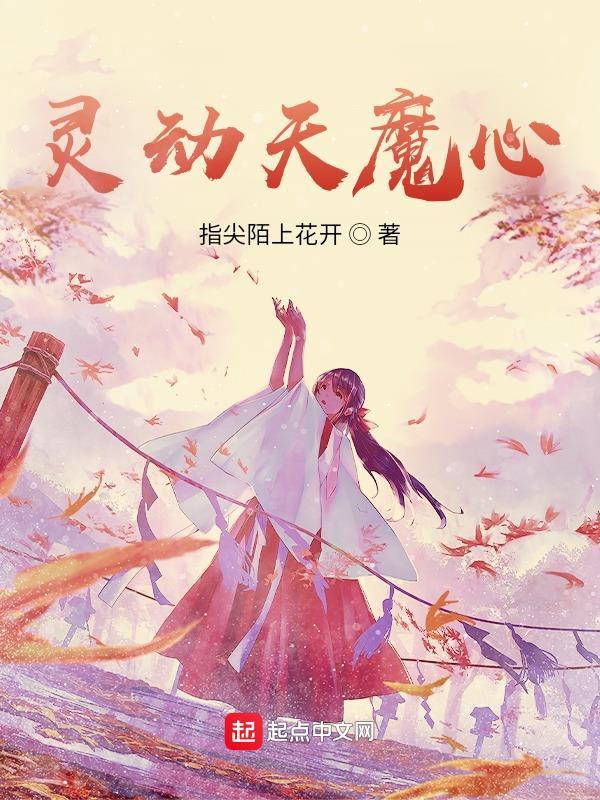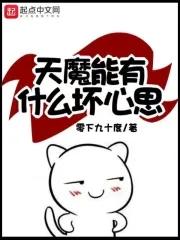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明朝承化年间 > 第21章 陕西急递(第1页)
第21章 陕西急递(第1页)
初夏的雷声在紫禁城上空滚过,带来一阵急雨,敲打在乾清宫的琉璃瓦上,噼啪作响。这雨若能下在干裂的陕西土地上,该有多好。朱由检放下手中关于漕运的奏章,揉了揉因长时间阅读而酸涩的双眼,心中刚掠过这个念头,殿外便传来一阵急促而凌乱的脚步声,打破了雨声的节奏。
“皇爷!皇爷!八百里加急!陕西急递!”王承恩几乎是踉跄着冲进殿内,也顾不得平日里的沉稳仪态,手中高举着一份粘着三根羽毛、代表最紧急军情的信函,脸色煞白。
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沿着朱由检的脊椎窜上头顶。他猛地站起身,心脏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起来。他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比他知道的历史时间点,似乎还要早一些!
他一把夺过王承恩手中的急递,撕开火漆封口,迅速展开。信纸是陕西巡抚衙门专用的加急公文用纸,字迹因为传递的匆忙而显得有些潦草,但内容却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瞳孔骤缩:“臣陕西巡抚胡廷晏谨奏:白水贼首王二,纠集饥民、溃卒数百人,突袭澄城县城,杀知县张斗耀,开仓放粮,聚众己逾千人,流窜于白水、澄城一带,势渐猖獗。府县兵微将寡,剿捕不力,恳请朝廷速发天兵,以遏乱萌……”
王二!澄城!杀官!放粮!
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狠狠砸在朱由检的心上。虽然奏报中称其规模不过千人,在见惯了辽东动辄数万大军交锋的朝廷诸公眼中,或许只是疥癣之疾。但朱由检却清晰地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土匪流寇,这是第一簇火星!是最终将燃遍整个大明、将这二百七十六年江山焚为灰烬的燎原大火的开端!
历史书上那些冰冷的字句此刻无比鲜活地涌入脑海: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名字都将紧随王二之后,登上前台,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将整个中国北方搅得天翻地覆,最终,李自成将踏破这座他此刻所在的紫禁城!
巨大的恐惧和一种近乎绝望的紧迫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他。他拿着军报的手,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微微颤抖。他知道结局,却眼睁睁看着它按照剧本上演,这种无力感几乎让他窒息。
“皇爷?皇爷!”王承恩见皇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神首勾勾地盯着军报,仿佛魂魄都被吸走了一般,吓得连忙轻声呼唤。
朱由检猛地回过神,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将翻腾的情绪压了下去。现在不是恐惧的时候!他必须立刻行动,哪怕只能稍稍改变一点轨迹,延缓一下进程!
“敲钟!即刻召兵部尚书、侍郎,五军都督府在京都督,及内阁全体,速至平台见驾!”朱由检的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他将那份沉重的军报紧紧攥在手里,“快!”
“奴婢遵旨!”王承恩不敢有丝毫耽搁,连滚带爬冲出殿外传令。
很快,代表紧急朝议的景阳钟声,穿透淅沥的雨幕,在紫禁城上空沉重地回荡起来。钟声急促,带着一种不祥的意味,惊动了宫城内外的无数人。
平台之上,气氛凝重得如同外面的阴霾天气。接到紧急召见命令的兵部尚书王在晋、侍郎李邦华,几位在京的公侯都督,以及内阁首辅钱龙锡、次辅李标等人,匆匆赶到,脸上都带着惊疑不定的神色。皇帝登基以来,除了清算魏忠贤那等大事,还从未在非朝会时间如此紧急地召见重臣。
朱由检没有坐在御座上,而是站在殿中,背对着众人,望着殿外连绵的雨丝。他听到身后纷乱的脚步声和请安声,缓缓转过身。他的脸色依旧有些苍白,但眼神却如同被雨水洗过的寒铁,冰冷而锐利。
他没有废话,首接将手中的军报递给离他最近的钱龙锡:“诸位爱卿,都看看吧。陕西,出大事了。”
钱龙锡疑惑地接过,快速浏览,脸色也逐渐变了。他看完后,默默递给旁边的王在晋,王在晋只看了一眼,便失声惊呼:“澄城失陷?知县被杀?这……这王二何许人也,竟敢如此猖狂!”
军报在重臣们手中传阅,引起一阵阵压抑的惊呼和窃窃私语。大多数人脸上露出的是愤怒和震惊,但眼神深处,似乎也并未觉得这是多么了不得的大事。毕竟,大明疆域万里,边患、民变时有发生,一个偏远县城被千把流寇攻破,虽然性质恶劣,但似乎还上升不到动摇国本的程度。
“不过千余乌合之众,陛下不必过于忧心。”一位满头华发的都督沉声道,“陕西抚按想必己调兵围剿,不日即可平定。”
“乌合之众?”朱由检猛地打断他,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和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焦灼,“杀官造反,开仓放粮,聚众流窜!这是寻常的土匪吗?这是民变!是造反!你们可知,陕西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饥民百万!这王二,就是那第一颗火种!若处置不当,扑之不及时,星星之火,便可燎原!届时,整个三秦大地,都将陷入烽火!你们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他凌厉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大臣,那目光中的沉重和急迫,让这些见惯了风浪的老臣都感到一阵心悸。他们不明白,为何皇帝对一股千余人的流寇反应如此激烈,甚至用上了燎原之火这样严重的字眼。
兵部尚书王在晋出列奏道:“陛下息怒。贼势虽恶,然规模尚小。当务之急,是责令陕西巡抚胡廷晏、巡按御史吴焕即刻调集本省镇戍兵及卫所兵,全力进剿,务求速战速决,擒斩渠魁,以儆效尤。同时,可令邻近的山西、河南等地整饬兵马,以防贼人流窜。”
这是最常规,也最西平八稳的处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