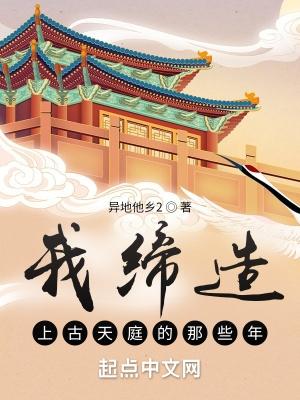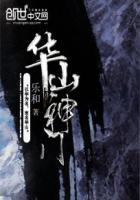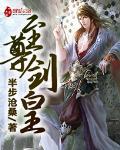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喂饱了千万粉丝英文 > 第41章 东极岛渔歌 东海尽头的鲜与静(第1页)
第41章 东极岛渔歌 东海尽头的鲜与静(第1页)
陆帆离开朱家尖时,晨雾还没完全散去。那雾不是城市里灰蒙蒙的霾,是带着海风湿气的薄纱,轻轻裹着整个南沙渔村。村口的枇杷树在雾里只剩模糊的绿影,叶子上挂着的露珠比米粒还小,风一吹就滚下来,砸在青石板路上,溅起针尖大的湿痕,很快又被晨雾笼住,只留下一点淡淡的水渍。阿妹姨站在枇杷树下,靛蓝色的渔家袄在雾里像一块深潭,乐乐躲在她身后,手里攥着那个能吹出声的海螺,鼓着腮帮子吹了一下,“呜呜”的低鸣在雾里飘得很远,像大海在轻轻送别。
“三轮车慢,你坐稳喽!”阿妹姨帮陆帆把帆布背包塞进车斗,又用绳子系了系——背包里装着阿妹姨给的鱼鲞和枇杷,鱼鲞是用旧报纸包的,外面还裹着一层塑料袋,怕被雾打湿;枇杷装在竹篮里,上面盖着枇杷叶,叶子上的露珠沾在篮子上,凉丝丝的。三轮车是半旧的,车斗里铺着一块蓝色粗布,上面绣着歪歪扭扭的鱼纹,是阿妹姨自己绣的。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的缝隙,那里长着浅绿的青苔,车轮压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像老渔民在低声说话。
车斗里的鱼鲞和枇杷渐渐散出味道。鱼鲞的咸鲜是沉的,像海底的礁石,带着一点阳光晒过的干香;枇杷的甜是轻的,像雾里的露珠,带着一点草木的清苦。两种味道混在雾里,飘在陆帆鼻尖,他低头摸了摸竹篮里的枇杷,果皮是暖黄色的,带着一点温度,是早上刚从树上摘的。“到了沈家门码头,记得买最早的船票,东极轮十点开,别错过了。”阿妹姨骑在前面,声音被风吹得有点飘,“东极岛的海比朱家尖蓝,海鲜也鲜,你去了一定要吃海鲜面,汤是用刚熬的鱼骨汤做的,熬得奶白,鲜得能掉眉毛!”
陆帆应着,靠在车斗的栏杆上,看雾里的渔村慢慢后退。石屋的黑顶在雾里露出来,像浮在海上的小岛;院子里的渔网挂在竹篱笆上,被风吹得轻轻晃,像蓝色的帘子;偶尔有渔民打开门,手里拿着搪瓷盆,盆里装着要洗的衣服,看到阿妹姨的三轮车,笑着喊一声“阿妹,送客人啊”,阿妹姨也笑着应“是啊,去东极岛”,声音在雾里撞在一起,又慢慢散开。
到了朱家尖客运站,阿妹姨帮陆帆把行李搬上前往沈家门的大巴,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是她用铅笔写的东极岛攻略:“庙子湖岛住老郑家(渔民,人好),海鲜面吃秀琴家的,看日出去东福山岛,五点起床。”字迹歪歪扭扭的,有的笔画还断了,是她昨天晚上就写好的。“找不到老郑家,就问渔民,他们都认识。”阿妹姨把纸条塞给陆帆,又摸了摸他的背包,“鱼鲞别受潮,枇杷尽快吃,放久了会坏。”
大巴发动时,陆帆从车窗里挥手,阿妹姨和乐乐还站在站台上,乐乐举着海螺,又吹了一声“呜呜”的响,阿妹姨笑着挥手,雾里的身影渐渐变小,最后成了一个小小的蓝点。
大巴沿着海岸线行驶,雾慢慢散了。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洒在海面上,把海水染成了浅金色。一开始,海水还是朱家尖附近的浅蓝,带着一点浑浊的黄,像掺了牛奶的蓝墨水;往沈家门方向走,海水渐渐变深,成了透亮的蓝,像一块被阳光晒暖的蓝宝石;再往远看,海天交接的地方,海水成了深邃的蓝,像一块藏在海底的翡翠。
陆帆靠在车窗上,翻看着在朱家尖拍的照片。相机里,阿妹姨弯腰挖花蛤时,靛蓝色的渔家袄被风吹得贴在背上,手里的小铲子陷在沙子里,周围散落着几个刚挖出来的花蛤;乐乐举着小海螺,笑得露出了两颗小虎牙,脸上沾着沙子,像个小花猫;院子里的枇杷树结满了金黄的果子,阳光落在果子上,泛着油光;沙滩上的小孔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芝麻,旁边的小螃蟹跑得飞快,留下一道细细的沙痕……每一张照片都带着阳光和海风的味道,让他想起阿妹姨说的“大海是慷慨的”——大海给了渔民鲜美的海鲜,给了沙滩温暖的阳光,也给了陌生人真诚的相遇。
大巴到沈家门码头时,己经是上午九点。码头比前几天更热闹,像一锅刚烧开的水,满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码头上的海鲜摊位沿着路边摆了一排,泡沫箱里的冰块冒着白气,把周围的空气都染得凉丝丝的。带鱼的银鳞在晨光里反光,像一把把小刀子;梭子蟹的青黑壳上带着黄色的绒毛,有的还在动,大钳子敲在箱子上,发出“咚咚”的声响;虾虎装在网兜里,活蹦乱跳的,偶尔有几只跳出网兜,落在青石板路上,“哒哒”地蹦着,摊主阿姨赶紧弯腰捡起来,嘴里念叨着“小祖宗,别跑啊”,引得周围的游客笑起来。
穿碎花裙的姑娘蹲在虾虎摊位前,手里拿着手机,对着虾虎拍个不停,男朋友在旁边帮她拎着包,笑着说“买一点吧,晚上煮着吃,我给你剥壳”;戴眼镜的老爷爷站在带鱼摊位前,手里拿着一根手指,比着带鱼的宽度,问摊主“这带鱼新鲜吗?”,摊主大叔赶紧说“刚靠岸的,你看这眼睛,多亮”,说着就拿起一条带鱼,指着鱼眼——鱼眼是黑色的,很有神,没有一点浑浊;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婴儿车里的宝宝伸着小手,想去抓摊位上的花蛤,妈妈赶紧拦住,笑着说“宝宝乖,花蛤会夹手哦”。
陆帆跟着人群往“东极轮”的检票口走,手里的帆布背包被阳光晒得暖暖的。“东极轮”是白色的,船身长约二十米,船头挂着一面鲜红的国旗,在海风里猎猎作响,国旗的边角被风吹得卷起来,是常年在海上航行的痕迹。船身上写着“舟山群岛东极旅游”,字体是蓝色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安全第一,服务至上”。
检票上船时,船员笑着说“欢迎去东极岛”,手里的检票钳“咔嚓”一声,在船票上留下一个小孔。陆帆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座位是蓝色的,上面铺着浅灰色的坐垫,坐上去软软的。旁边的座位上,一个穿着蓝色救生衣的小男孩正趴在窗沿上,看着外面的渔船,嘴里念叨着“爸爸,船什么时候开啊?我想去看灯塔”,他爸爸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本《东极岛旅游指南》,笑着说“快了,等会儿就能看到灯塔了”。
船缓缓驶离沈家门码头时,陆帆趴在窗沿上,看着船尾激起的浪花。浪花是雪白色的,卷着细小的泡沫,像一条长长的丝带,跟着船走了很远。偶尔有海鸥跟着浪花飞,翅膀掠过水面,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然后又展翅飞向天空,发出“咕咕”的叫声,像在和船打招呼。
海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海藻的清苦和海水的咸意。风里还夹杂着一点渔船上的柴油味,一点海鲜摊位的腥味,还有一点游客身上的香水味,这些味道混在一起,成了沈家门港独有的气息。陆帆把窗户打开一点,海风更大了,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头发被风吹得贴在脸颊上,带着一点咸意,像刚吃过海鲜的味道。
“小伙子,第一次去东极岛?”邻座的大叔笑着问。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渔民服,袖口磨出了毛边,手腕上戴着一块旧手表,表盘上的数字己经模糊了,表带是棕色的皮质,也磨得发亮。他手里拿着一个搪瓷杯,杯子上印着“舟山渔政”的字样,杯沿有一道缺口,里面装着热茶,冒着白气。
陆帆点点头,笑着说“是啊,听阿妹姨说东极岛的海鲜很鲜,想来尝尝”。
“阿妹姨?是朱家尖南沙渔村的陈阿妹吧?”大叔眼睛一亮,“我认识她,她老公以前和我一起出过海,是个捕鱼的好手!”大叔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烟,是舟山本地的“东海烟”,烟盒是蓝色的,上面印着一条带鱼。他抽出一根烟,却没有点燃,而是夹在耳朵上,“船上不让抽烟,我这烟是给老郑带的,他是我兄弟,在庙子湖岛开民宿。”
大叔叫郑建国,大家都叫他老郑,是东极岛庙子湖岛的渔民,以前靠捕鱼为生,现在年纪大了,开了家民宿。“东极岛不是一个岛,是一群岛的统称,主要有庙子湖岛、青浜岛、东福山岛。”老郑喝了一口热茶,搪瓷杯碰在嘴边,发出“叮”的轻响,“庙子湖岛是主岛,最热闹,有码头、有市场;青浜岛的石屋最有特色,一层叠一层,像布达拉宫,大家都叫它‘海上布达拉宫’;东福山岛是我国最东边的有人居住的岛屿,每天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就是那儿,好多人专门去看日出。”
老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己经有点泛黄,边缘也磨破了。照片上,东福山岛的红白灯塔矗立在海边的礁石上,背景是初升的太阳,金色的光芒洒在海面上,像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灯塔旁边,年轻的老郑穿着渔民服,手里拿着一个渔网,笑得露出了牙齿。“这张照片是我三十年前拍的,那时候我还在东福山岛当守塔人,每天晚上添煤油,早上擦灯罩。”老郑摸着照片,眼神里带着怀念,“这个灯塔是东极岛的标志,以前渔民出海全靠它指路,晚上看到灯塔的光,就知道家的方向了。现在灯塔改成电灯了,不用人守了,但我还是经常去看它。”
陆帆接过照片,指尖碰到照片的边缘,有点粗糙,是常年的痕迹。照片上的灯塔红白相间,每一道红每一道白都很整齐,是用油漆刷的,上面还有一点海风留下的痕迹,有点褪色。海面上的浪花是白色的,拍在礁石上,溅起小小的水花,像珍珠一样。“这张照片真好看,我也想去东福山岛看灯塔。”陆帆把照片还给老郑,心里满是期待。
“没问题,明天我带你去。”老郑把照片放回口袋里,又喝了一口热茶,“东福山岛的日出也好看,早上五点多,太阳从海平面上跳出来,金色的光洒在海里,像一条金色的路,从海里一首铺到你脚下,可壮观了!”
船行驶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抵达庙子湖岛。码头不大,用青灰色的石板铺成,石板上有不规则的纹路,是海浪长期冲刷的痕迹。码头边的礁石是黑色的,表面很粗糙,上面长着绿色的青苔,海浪拍在礁石上,溅起白色的浪花,发出“哗哗”的声响,浪花落在石板上,打湿了一片,凉丝丝的。
岸边停着几艘小渔船,都是木制的,船身是棕色的,船头挂着红色的小灯笼,有的渔船上还晾着渔网,是深蓝色的,渔网上挂着小小的贝壳,是以前捕鱼时缠上的,现在成了装饰。渔民们正忙着把刚捕捞的海鲜卸下来,他们穿着蓝色的救生衣,皮肤晒得黝黑,手里拿着网兜,把海鲜倒进泡沫箱里。带鱼的银鳞在阳光下反光,虾虎的大钳子在箱子里“哒哒”地响,淡菜的紫色外壳堆在一起,像一堆小小的宝石。
“走,我带你去我家民宿,就在码头附近,走路五分钟就到。”老郑拎着陆帆的帆布背包,肩膀一沉,又很快稳住——背包里装着鱼鲞和枇杷,还有相机,有点沉。老郑的手很粗糙,指关节很大,手掌上有很多老茧,是常年捕鱼留下的痕迹,他拎背包的时候,手指紧紧攥着背包带,怕背包掉下来。
沿着码头边的小路走,小路是用石头铺的,石头之间的缝隙里长着浅绿的小草,偶尔有几朵白色的小花开在草里,像星星一样。小路两旁是石屋,是用岛上的黑礁石砌的,墙壁上有不规则的纹路,是海浪和海风留下的痕迹。屋顶铺着青灰色的瓦片,瓦片上压着石头,防止被海风刮走。有的石屋门口挂着红灯笼,灯笼上写着“民宿”两个字,有的门口挂着渔网,有的门口摆着几盆仙人掌,仙人掌种在破瓷盆里,瓷盆上画着小鱼,叶子长得很肥,是深绿色的,上面长着细细的刺,在阳光下泛着光。
石屋里偶尔传来渔民的声音,有的在炒菜,锅里发出“滋滋”的声响,香味飘在小路上,是海鲜的鲜;有的在唱歌,是舟山渔歌,调子悠扬,带着大海的辽阔;有的在聊天,舟山话的调子软软的,像海浪一样,一句接一句,很热闹。
老郑的民宿叫“渔家乐”,门口挂着一块木牌,是用岛上的松树做的,上面刻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字体是黑色的,有点歪歪扭扭的,是老郑自己刻的。木牌旁边挂着一串贝壳,是白色的,风一吹,贝壳互相碰撞,发出“叮叮”的声响,像风铃一样。
院子里种着几棵椰子树,树干很粗,上面有一圈圈的年轮,是海风和阳光留下的痕迹。树叶是羽状的,在风里轻轻晃,影子落在地上,像跳动的碎金子。树下摆着几张竹椅和一张石桌,竹椅是淡绿色的,上面有细细的竹纹,石桌是青灰色的,表面很光滑,是常年使用的痕迹。石桌上放着一个刚编到一半的竹篮,竹条是淡绿色的,带着一点潮气,旁边放着一把竹刀,是编竹篮用的。
“这是我老伴编的,她以前也是渔民,现在没事就编竹篮,卖给游客当纪念。”老郑说着,朝屋里喊了一声“老婆子,来客人了!”,声音在院子里回荡,又飘到屋里。
屋里传来一阵“哒哒”的脚步声,一个穿着碎花衬衫的阿姨从屋里走出来。阿姨约莫五十多岁,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绾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额角有几颗雀斑,像撒了一把芝麻。她手里拿着一块刚揉好的面团,面团是白色的,上面沾着一点面粉,她的手上也沾着面粉,像撒了一层薄薄的雪。“来啦来啦!”阿姨笑着说,声音软软的,带着浓浓的舟山口音,“小伙子,一路辛苦了,先坐会儿,我去给你煮碗海鲜面,刚从码头买的虾虎,鲜得很!”
阿姨叫秀琴,是老郑的老伴。她把面团放在案板上,案板是木制的,上面有很多细小的纹路,是常年切菜留下的痕迹。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擦了擦手上的面粉,又给陆帆倒了一杯水,杯子是粗陶的,上面印着一朵荷花,“这水是岛上的井水,凉丝丝的,你喝一口解解渴。”
陆帆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井水。井水很凉,带着一点甜味,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矿泉水,咽下去后,喉咙里很舒服,旅途的疲惫也消了一半。他坐在竹椅上,打开相机,把船上拍的海景导出来。相机里,海面上的浪花是雪白色的,海鸥的翅膀掠过水面,留下一道浅浅的水痕,远处的小岛像绿色的宝石,镶嵌在蓝色的海里……每一张照片都带着海风的味道,让他想起老郑说的“东极岛好啊”。
秀琴在厨房里忙碌着,传来“哗哗”的水声,是她在清洗海鲜。“我们东极岛的海鲜,不用放太多调料,清水煮煮就好吃。”秀琴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尤其是虾虎,现在正是肥的时候,里面全是黄,你等会儿尝尝就知道了。”
老郑坐在陆帆旁边,给陆帆讲东极岛的故事。“以前东极岛全靠捕鱼为生,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晚上靠煤油灯照明,喝水要去井里挑。渔民们早上天不亮就出海,下午才回来,有时候遇到大风大浪,好几天都回不来。”老郑的手指在石桌上轻轻敲着,“有一次我和我弟出海,遇到大风,船帆被吹破了,我们俩轮流划桨,划了一夜才靠岸。到家的时候,我老婆哭红了眼睛,煮了一锅海鲜面,汤都熬稠了,我吃了两大碗,才觉得活过来了。”
“现在不一样了,旅游业发展起来了,岛上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好多渔民都开了民宿,日子比以前好多了。”老郑笑着说,“以前我儿子不喜欢岛上的生活,非要去城里打工,现在也回来了,帮我们打理民宿,他说‘岛上的空气好,海鲜鲜,比城里舒服’。”
正说着,秀琴端着一碗海鲜面从厨房里走出来。碗是粗陶的,很大,碗沿有一圈淡蓝色的花纹,是秀琴自己画的。面条是手擀的,切得很细,躺在碗里,上面铺着三只虾虎、一把淡菜、几个蛏子,还有一个荷包蛋。虾虎的壳是青黑色的,上面有黄色的斑点,淡菜的壳是紫色的,蛏子的壳是白色的,荷包蛋的蛋黄是溏心的,像一块小小的太阳。汤是奶白色的,飘着葱花和香菜,香气扑鼻,像刚掀开的蒸笼,热气里全是海鲜的鲜。
“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秀琴把筷子递给陆帆,筷子是竹制的,上面有细细的竹纹,“这面条是我早上刚擀的,你尝尝,有没有嚼劲。”
陆帆接过筷子,夹了一根面条。面条咬在嘴里很有嚼劲,裹着鱼汤的鲜,没有一点硬芯,是刚煮好的样子。他夹了一只虾虎,用手捏住虾虎的头,轻轻一掰,虾虎的壳就开了,里面的肉是白色的,带着淡淡的粉色,咬了一口,鲜汁立刻充满了口腔,肉质紧实又弹牙,里面的黄是金黄色的,像融化的黄油,甜得很,没有一点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