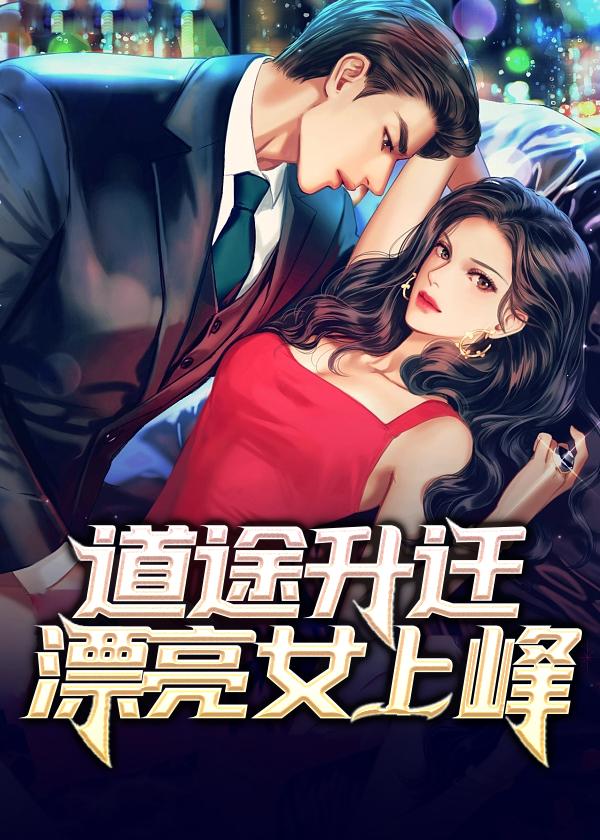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app > 第25章 诸老大粽香裹着太湖的岁月(第2页)
第25章 诸老大粽香裹着太湖的岁月(第2页)
王阿婆看到陆帆手里的粽子,笑着对他说:“小伙子,你第一次来吃吧?诸丫头家的粽子可是我们南浔的招牌,我小时候就吃,那时候还是她奶奶在包,现在轮到她了,味道一点没变。以前过节的时候,我们家都会来买十几个,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粽子,喝雄黄酒,热闹得很。”
“是啊,王阿婆,”诸阿姨接过话茬,语气里带着点怀念,“我奶奶那时候包粽子,要凌晨三点就起来,烧柴火煮粽子,整个西街都能闻到粽香。那时候南浔的丝商多,很多丝商要去上海、苏州做生意,都会来我们家买粽子带在路上吃,说路上吃着方便,还能想起家里的味道。有个上海的丝商,每次来都要买五十个,用油纸包好,装在藤箱里,带到上海给他的客户尝,后来他的客户也专门来南浔买我们家的粽子。”
诸阿姨指着墙上挂的一张老照片,照片己经有些泛黄,边缘也有些磨损,照片里是一位穿着旗袍的老奶奶和一位穿着长衫的老爷爷,他们站在诸老大的铺子前,手里各拿着一个粽子,笑容慈祥。铺子的门面上挂着和现在一样的“诸老大”老匾,只是那时候的门还是木门,上面没有贴对联,“这张照片是1920年拍的,照片里的是我太爷爷和太奶奶。我太爷爷诸光潮以前是个丝商,后来看到南浔人喜欢吃粽子,而且丝商往来多,需要方便携带的食物,就开了这家粽子铺。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那时候上海的报纸还报道过我们家的粽子,说‘南浔诸老大,粽香满江南’。”
她又指着另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包粽子,周围围着几个小孩,“这是我奶奶,那时候她才三十多岁,正在教我妈妈包粽子。以前我们家的粽子都是手工包的,一天最多包两百个,我奶奶、我妈妈,还有几个邻居阿姨一起包,从早忙到晚。现在虽然有了机器能帮忙拌馅、煮粽子,但我们还是坚持手工包扎,手工包扎的粽子更紧实,稻草的香味能更好地渗进糯米里,机器包的没有这个味道。”
陆帆看着照片,心里忽然有些触动。他想起自己小时候,每到端午节,奶奶都会在家包粽子,也是用青箬叶,也是用稻草捆,煮粽子的时候,整个屋子都飘着粽香。奶奶包粽子的手法和诸阿姨很像,手指翻飞,一会儿就包好一个三角粽。那时候他总在旁边看着,偶尔还会伸手帮忙,却总是把粽子包得歪歪扭扭,稻草也捆不紧,奶奶就笑着教他,“慢慢来,包粽子要用心,急不得。”
现在奶奶不在了,他再也吃不到奶奶包的粽子了,没想到在南浔的诸老大,能吃到这么像奶奶味道的粽子,还能听到这么多关于粽子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有传承,有坚守,有温情,像太湖的水一样,温柔而绵长,流淌了一百多年,还在继续。
陆帆吃完最后一口粽子,觉得胃里暖暖的,心里也满满的。他走到柜台前,对诸阿姨说:“诸阿姨,给我装十个蛋黄肉粽,我带回去给家人和朋友尝尝,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南浔的味道,感受一下百年老店的传承。”
“好嘞!”诸阿姨笑着拿出一个纸盒子,盒子是白色的,上面印着“诸老大”的logo,还有一片青箬叶的图案,“这些粽子都是刚煮好的,你回去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能放一个星期。吃的时候不用解冻,首接放在蒸锅里,水开后蒸十分钟就好,味道和刚出锅的一样。”
她一边说,一边把粽子一个个放进盒子里,每个粽子都用油纸包好,再用稻草捆了一下,“这样包着,能保持粽子的香味,也不容易粘在一起。”她还特意找了一张纸条,用钢笔写下“加热方法:水开后蒸十分钟即可,建议热吃”,字迹娟秀,和竹篮上的标签一样,然后把纸条放进盒子里。
陆帆付了钱,接过纸盒子,盒子沉甸甸的,不仅装着十个粽子,还装着诸老大一百多年的传承,装着南浔的温情。他对诸阿姨说:“谢谢您,诸阿姨,不仅让我吃到了这么好吃的粽子,还让我听到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不用谢,”诸阿姨笑着送他到门口,“小伙子,下次来南浔,记得再来吃粽子,我给你留刚出锅的,再给你讲我太爷爷当年开铺子的故事。”
“好的,诸阿姨,我一定会再来的!”陆帆笑着挥手,心里满是留恋。
走出诸老大,西街的阳光更暖了,把影子拉得很长。陆帆提着装满粽子的纸盒子,沿着河边往客栈走。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到水底的水草在轻轻晃动,岸边的垂杨柳把枝条垂到水面上,风一吹,枝条就跟着摆动,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细小的涟漪。偶尔有小鱼从水里跳出来,溅起一圈圈水花,很快又消失在水里,只留下一圈圈波纹,慢慢扩散开来。
他想起这几天在湖州的经历,像一场温暖的梦——在张记面馆,张爷爷给他煮双交面,讲爆鱼的做法,还送他刚炸好的爆鱼,那爆鱼的酥脆里藏着老手艺的坚守;在丁莲芳,丁奶奶教他包千张包,讲千张包的传承故事,还送他新鲜的千张皮,那千张皮的软嫩里藏着手艺人的温情;在周生记,周老板给他做干挑馄饨,讲馄饨的秘方,还送他自制的辣油,那辣油的香辣里藏着市井的爽朗;在诸老大,诸阿姨给他吃刚出锅的粽子,讲诸老大的百年历史,那粽子的香甜里藏着岁月的温柔。
这些手艺人,就像南浔的老槐树,默默守护着一份份味觉记忆,把岁月的味道一代代传下去。他们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精致的包装,却用最朴素的坚守,最真诚的用心,让每一份美食都充满了温度,让每一个来到南浔的人,都能感受到这里的温情。
走到客栈门口,王叔正在院子里修剪月季。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褂子,手里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把枯萎的花瓣剪掉,月季的清香在院子里漫开。看到陆帆,他停下手里的活,笑着问:“小伙子,粽子买了?看你手里的盒子,是诸丫头家的吧?”
“是啊,王叔,您也知道诸老大?”陆帆笑着说,走进院子里。
“当然知道!我们南浔人谁不知道诸老大啊!”王叔放下剪刀,擦了擦手上的汗,“我小时候就吃诸老大的粽子,那时候还是诸丫头的奶奶在包,现在轮到诸丫头了,味道一点没变。我孙子每次从外地回来,都要我给他买诸丫头家的蛋黄肉粽,说‘爷爷,我就要吃诸奶奶包的,别的地方的不好吃’。”
他看着陆帆手里的盒子,又问:“准备走了?下一站去哪里?”
“下一站去嘉兴,”陆帆说,“听说嘉兴的粽子也很有名,想去尝尝,看看和南浔的诸老大有什么不一样。”
“嘉兴的粽子是不错,味道也很鲜,”王叔笑着说,“但是我们南浔的诸老大,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太湖的灵气,有南浔人的坚守,这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你要是下次再来南浔,一定要再来尝尝诸丫头的粽子,还有张记的双交面,丁莲芳的千张包,周生记的馄饨,这些都是我们南浔的味道,不能错过。”
“我会的,王叔,”陆帆点点头,心里满是留恋,“这次来南浔,我收获了很多,不仅吃到了好吃的美食,还认识了很多温暖的人,听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我一定会再来的。”
陆帆走进客栈,开始收拾行李。他把诸阿姨给的粽子放在行李箱的最上面,小心地垫上软布,防止挤压;把丁奶奶给的千张皮用油纸包好,放进保鲜袋里;把周老板给的辣油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避免洒出来;把张爷爷给的爆鱼用保鲜盒装好,放在行李箱的侧面。
每一样东西,都对应着一个故事,一个温暖的人。看到千张皮,他就想起丁奶奶教他包千张包时的耐心;看到辣油,他就想起周老板爽朗的笑容;看到爆鱼,他就想起张爷爷慈祥的眼神;看到粽子,他就想起诸阿姨温柔的话语。这些东西,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他在南浔最珍贵的回忆,是手艺人送给她的礼物,是岁月送给她的温柔。
他打开笔记本,拿出钢笔——钢笔是出发前妈妈给他买的,笔身上刻着“平安”两个字,妈妈说希望他一路平安,能在旅途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在笔记本上写下:
“湖州的味道,是太湖边的糯米香,是青箬叶的清新,是五花肉的油润,是手艺人的坚守,是老街上的烟火气。从张记双交面的骨汤鲜,到丁莲芳千张包的豆香软;从周生记馄饨的酱汁暖,到诸老大粽子的箬叶香,每一口都是湖州的精致,每一段故事都是岁月的温柔。
南浔的古镇不大,却藏着最动人的味道,最温暖的人。这里的手艺人,用一百年的坚守,把太湖的灵气、水乡的温情,都包进了粽子里,煮进了汤里,揉进了面里。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最朴素的坚持,让一份份美食跨越了时光,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离开南浔的时候,阳光正好,粽香还在嘴角,心里满是留恋。我知道,我会永远记得这里的味道,记得这里的人,记得这里的岁月。湖州的故事,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留在我的书稿里,成为我旅行中最温暖的一页。”
写完,陆帆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帆布包里。他拉上行李箱,最后看了一眼客栈的房间——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桌子上,桌子上还放着他昨天喝剩下的安吉白茶,茶杯里的茶叶己经沉底,却还留着淡淡的茶香。
他走出客栈,王叔还在院子里修剪月季,看到他,笑着挥手:“小伙子,路上小心,记得常来南浔玩!”
“再见,王叔!”陆帆挥手告别,心里满是不舍。
他沿着石板路往古镇外走,回头看了一眼西街的方向,诸老大的铺子还亮着暖黄的灯,隐约能看到诸阿姨忙碌的身影。路边的老槐树上,几只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像是在送别。
下一站是嘉兴,那里有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美食。但陆帆知道,湖州的味道,南浔的温情,会永远留在他的心里,像一颗温暖的种子,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当想起,都会让人心里发暖。
太湖的水还在静静地流,南浔的粽香还在轻轻地飘,一百年的传承,还在继续。而陆帆的旅行,也还在继续——带着湖州的温暖,带着手艺人的温情,去寻找更多的味道,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