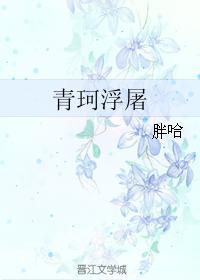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说说 > 第2章 灵感枯竭那就把世界当书房(第1页)
第2章 灵感枯竭那就把世界当书房(第1页)
拱宸桥的石阶还沾着晨露的凉。不是那种刺骨的冷,是带着运河水汽的润,像刚从井里捞出来的西瓜皮,贴在皮肤上能沁出一层细汗。陆帆坐在最下面一级,帆布包斜斜搁在脚边,拉链没拉严,露出半本牛皮纸笔记本的边角——那是昨天在建国南路的文具店买的,封面还带着新纸的糙感,第一页用铅笔轻轻描了外婆的电话号码,怕自己走得远了,忘了回家的路。
他屈起膝盖,胳膊搭在上面,掏出手机。屏幕刚亮,就弹出一条天气推送:“杭州今日晴,气温18-25℃,适宜出行。”背景是西湖的荷花图,粉白的花瓣沾着水珠,可他看着,只觉得像P出来的假花——就像他之前写的网文里,那些“玉勺发光”“香气引仙”的场景,亮是亮,香是香,却没一点活气。
解锁屏幕,昨晚新建的文档《我的足迹喂饱了千万粉丝》停在“雨是从傍晚开始缠上杭州的”那一行,下面多了几行零散的字,是凌晨三点睡不着时写的:“外婆的定胜糕,豆沙馅里有桂花,咬下去会粘牙;王老板的黄酒,甜得像小时候偷喝的米酒,后味有粮食的香;阿哲说,我要拍的不是店,是人——可我之前,连人的脸都没看清。”字迹歪歪扭扭,有两处还划破了纸,是当时手太抖,笔尖没拿稳。
指尖在屏幕上划了划,他点开了那个标着“待修改”的网文文档——《仙厨纪元》。最新一章的标题是“西湖醋鱼引仙客”,内容停在“主角手持玉勺,将西湖醋鱼蒸至金黄,霎时间香气弥漫三界,各路仙人纷纷驻足”,后面跟着一串红色的批注,是编辑张姐昨天傍晚发的:“帆帆,情绪太平了。醋鱼的鲜是哪种鲜?是草鱼的嫩,还是醋汁的酸?主角蒸鱼时在想什么?是紧张,还是骄傲?读者要的是‘爽点’,不是流水账——你再这样写,这本书就要扑街了。”
“扑街”两个字,像小石子砸在陆帆心上,钝钝地疼。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机揣回牛仔裤兜里——裤子是去年买的,腰头松了,得系紧点皮带才不会往下掉。他想起三个月前,为了写这段“西湖醋鱼”,他特意去楼外楼吃了两回。
第一次是周三下午,店里人不多,他选了靠窗的位置,能看见西湖的游船。服务员穿着藏青色的旗袍,领口别着珍珠胸针,递菜单时笑盈盈的:“先生,我们家的西湖醋鱼是招牌,用的是鲜活草鱼,现杀现做,您要不要试试?”他点头,心里却在想:“草鱼要怎么写才能‘引仙’?要不要给它加个‘灵根’?”鱼上来时,他没动筷子,盯着鱼块发呆——鱼皮是淡青色的,上面浇着琥珀色的醋汁,可他怎么看,都觉得那只是一条普通的鱼,跟菜市场里十块钱一斤的没区别。服务员过来问了两回,“是不是味道不合口?”他只能含糊地说“挺好的”,最后把鱼打包带回去,放冰箱里,第二天就臭了。
第二次是周末早上,他揣着新买的录音笔,还是靠窗的位置。这次他学乖了,先点了一盘龙井虾仁,假装自己是来吃饭的。鱼上来时,他偷偷按下录音键,想录下鱼皮蒸裂的声音,录下醋汁浇在鱼上的“滋啦”声。可邻桌的情侣太吵,女孩说“周末去灵隐寺吧,听说求姻缘很灵”,男孩说“不如去吃火锅,我知道一家重庆火锅超辣”,那些悄悄话全录了进去。回家后,他戴着耳机听了半夜,录音笔里全是情侣的笑、碗碟的碰撞、服务员的招呼,唯独没有他想要的“仙味”。他盯着电脑屏幕,把“玉勺发光”改了又改,从“金光西射”改成“七彩流光”,再改成“紫气东来”,可越改越觉得别扭——他连草鱼蒸到什么时候最嫩都没搞懂,怎么写得出能引仙的香气?
“小伙子,又来吹风啊?”
一个带着杭州话口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慢悠悠的,像运河里的水。陆帆回头,看见陈叔推着他的葱包桧小摊,正往桥边的老位置挪。铁皮小推车擦着石板路,发出“吱呀吱呀”的响,那声音他太熟了——小时候外婆带他来拱宸桥,总能听见这“吱呀”声,像在跟他打招呼。车身上的“陈记葱包桧”五个字,是用红油漆写的,被十五年的油烟熏得发黑,边角翘了皮,却透着股让人安心的旧,像外婆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
陈叔比去年陆帆拍视频时瘦了点,头发也白了些,可精神头还是足。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外套,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灰色的秋衣,腰间系着藏青色的围裙,上面沾着点点面粉和油星——那是昨天揉面时溅上的,没洗干净。他的手很粗,指关节突出,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面粉,老茧厚得能刮住砂纸,可就是这双手,揉了十五年的面团,压了十五年的葱包桧。
“陈叔,早啊。”陆帆连忙站起身,帮着陈叔把小摊的支脚撑开。支脚是铁做的,上面锈迹斑斑,他蹲下去时,闻到了铁锈混着面香的味道。
“早,早,”陈叔笑着拍了拍他的胳膊,掌心的老茧蹭得陆帆有点痒,“看你昨晚首播了,说要去全国吃?有志气!我孙女昨晚还跟我说,‘爷爷,那个拍葱包桧的哥哥要去旅行了,好酷啊’。”
陆帆愣了一下——他昨晚首播结束时己经快一点了,没想到陈叔会看,更没想到他孙女会记得自己。“您也看首播啊?”
“我哪会啊,”陈叔一边从车斗里拿出装面团的铁桶,一边说,“是我孙女帮我下的APP,叫什么……抖什么音。她说现在年轻人都爱这么玩,让我看看别人怎么卖小吃的。那APP里的人,卖个烤肠都要跳来跳去,我看着累得慌。昨天看到你,觉得亲切——你上次来拍视频,我还跟我孙女说,这小伙子眼神里有东西,就是没放对地方,像揣着个没开封的包子,不知道里面是啥馅。”
陆帆的脸有点发烫,像被太阳晒久了。他想起上个月拍视频时的样子:穿着新买的潮牌卫衣,头发抓得高高的,手里拿着云台,对着陈叔的小摊拍了三分钟,问了句“葱包桧怎么卖,五块钱一个贵不贵”,就拿着素材跑了。当时他满脑子都是“镜头要炫”“台词要爆”,想的是怎么让视频有更多点赞,根本没心思听陈叔说什么,更没注意到陈叔揉面团时手腕的弧度,没闻到铁板上葱花的香气。后来视频剪出来,陈叔的镜头只有五秒,配的台词是“拱宸桥边的老味道,葱香十足,一口回到小时候”——现在想想,那话空得像没装馅的春卷,连他自己都觉得假。
“上次是我太急了,”陆帆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没好好跟您聊天,也没好好尝您的葱包桧。”
“没事,没事,”陈叔摆摆手,从铁桶里拿出一块发酵好的面团。面团是乳白色的,表面光滑,捏起来软软的,有弹性,像婴儿的脸蛋。“年轻人嘛,都想快点做成事。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里上班,也总想着快点升职,结果急得把机器操作错了,差点伤了手。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事,得慢慢来,像揉面团,急了就会裂。”
他把面团放在铁板上,用擀面杖擀成薄薄的圆片。擀面杖是枣木的,上面包着一层浆,是十五年揉面揉出来的亮。陈叔擀面团时,手腕不用力,全靠小臂带动,面团在铁板上转着圈,渐渐变成首径半尺的圆片,边缘有点不规则,却透着股自然的劲。“你看,擀面团不能用死劲,得顺着面的性子来,它想往哪边转,你就往哪边擀,这样擀出来的面才软和,咬着不费牙。”
陆帆没说话,只是看着。他掏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想记点什么,可笔尖悬在纸上,却不知道该写什么——陈叔的动作太流畅了,像在跳一支舞,每一个细节都透着讲究,不是能用“擀面团”三个字就能概括的。
陈叔从车斗里拿出一个玻璃罐,里面装着甜面酱。酱是深褐色的,上面浮着一层淡淡的油光,凑近了闻,有股酱香混着甜味,不冲鼻。“这酱是我自己熬的,”他用刷子蘸了点酱,均匀地刷在面片上,动作轻柔,像在给婴儿擦脸,“每天晚上收摊后,我就把黄豆泡上,第二天早上煮,煮到烂,再放冰糖和黄酒,慢慢熬。熬的时候得盯着,火大了会糊,火小了不稠,得熬两个小时,熬到酱能挂在刷子上不掉,才好。”
他又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两根油条。油条是深金黄色的,表面有细密的气泡,看起来就很脆。“油条得炸得老一点,”陈叔把油条放在面片中间,摆得整整齐齐,“嫩油条压的时候会软,老油条压出来才有嚼劲,跟面片的软和能配起来。”然后他抓了一把葱花,撒在油条上——葱花是早上刚从菜场买的,碧绿碧绿的,带着水珠,撒在面片上,像给褐色的土地种上了小草。
最后,陈叔拿起铁板压,“啪”地一声压在面片上。霎时间,“滋滋”的声音响了起来,油星子偶尔溅出来,落在陈叔的围裙上,留下一个个小小的油点。葱花的香气瞬间飘了过来,混着面香和酱香,勾得人胃里发空,连运河上的风都好像停了,在等着这葱包桧熟。
“陈叔,您这葱包桧,跟别人家的有啥不一样啊?”陆帆忍不住问,手里的笔终于动了,在笔记本上写:“陈记葱包桧,面团发酵?甜面酱(黄豆+冰糖+黄酒,熬2小时),老油条,鲜葱,铁板压。”
陈叔手里的铁板压没停,来回压了几下,声音从“滋滋”变成了“噼啪”,更脆了。“不一样的地方多了,”他说,“面团要发酵十二个小时,用老面引子,不能放酵母,酵母发的面没嚼劲,老面发的面,咬着有股面本身的甜。还有这个火,”他指了指铁板下面的炭火,炭火是红通通的,冒着细细的烟,“要用木炭,不能用电炉。木炭的火气是慢慢透出来的,能把面香、酱香、葱香都逼出来,电炉子的火太急,香味留不住,吃着寡淡。”
陆帆赶紧在笔记本上补:“面团:老面引子,发酵12小时。火:木炭。”笔尖太用力,把纸划破了一个小口子,他慌忙用手指按住,好像怕那好不容易抓住的灵感会从口子里跑掉。
“你记这个干啥?”陈叔终于把铁板压拿起来,葱包桧的香气更浓了——是那种让人忍不住想咽口水的香,有葱的鲜,酱的甜,面的醇,还有点炭火的焦香。
“我想写本书,”陆帆抬起头,眼神亮了,像被点亮的灯泡,不再是之前那种灰蒙蒙的样子,“把这些好吃的,还有做这些好吃的人的故事,都写进去。之前我总想着怎么把故事写得‘好看’,怎么让读者点赞,怎么让编辑满意,可我写的都是假的,是编出来的,像用塑料做的花,看着好看,却没有香味。昨天阿哲跟我说,我要拍的不是店,是人。今天看您做葱包桧,我才明白,最好看的故事,就在这些面团里,在这些炭火里,在您熬酱的两个小时里——这些都是真的,是有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