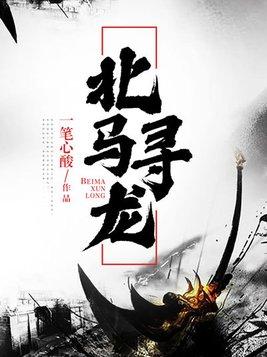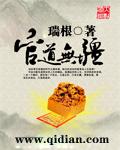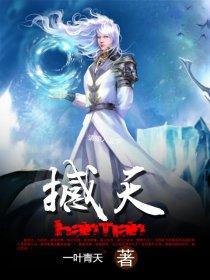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说说 > 第72章 毛豆腐的蜕变徽州智慧的发酵艺术(第2页)
第72章 毛豆腐的蜕变徽州智慧的发酵艺术(第2页)
“发酵房里的温度要保持在二十到二十五度之间,湿度要在七十左右,”陈师傅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老式温度计和湿度计,温度计的指针正好指在二十二度,湿度计的指针指在七十一,“温度太高了,豆腐容易烂,还会滋生杂菌,长出来的菌丝是黑色的,不能吃;温度太低了,菌丝又长不出来,豆腐还是原来的样子。湿度也一样,太高太低都不行。”
陈师傅拿起一个放在最上面的木盒,打开盖子,里面的豆腐表面己经长出了细细的菌丝,是纯白色的,像一层薄薄的绒毛,覆盖在豆腐表面,看起来很柔软,像天鹅绒一样。“你看,这就是‘毛’,”陈师傅用手指轻轻碰了碰菌丝,动作很轻,怕把菌丝碰掉,“要等菌丝长到一厘米左右,颜色从白色变成淡黄色,毛豆腐就做好了。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天,这三天里,我每天都会来检查两次,看看温度和湿度,还要看看菌丝的生长情况,一点都不能大意。”
陆帆凑近看,菌丝细细的,密密的,均匀地覆盖在豆腐表面,没有一点杂色,豆腐的边缘也没有腐烂的痕迹。他忍不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菌丝软软的,有点像棉花,却比棉花更细腻,碰过之后,手指上还留着淡淡的香气。“以前没有温度计和湿度计的时候,我爷爷就靠手感和经验判断,”陈师傅放下木盒,眼里带着敬佩的神情,“他说,好的毛豆腐,菌丝要‘密而不疏,黄而不黑’,凭着这两句口诀,他做了一辈子毛豆腐,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陈师傅从一个放在中间层的木盒里拿出几块己经发酵好的毛豆腐,菌丝己经变成了淡黄色,看起来很均匀,像一层薄薄的琥珀色绒毛覆盖在豆腐上。“现在就给你煎一块尝尝,让你看看做好的毛豆腐是什么味道,”他说着,抱着木盒走到院子里的灶台边,把木盒放在旁边的石桌上,然后点燃了柴火,锅里倒了一点本地榨的菜籽油。油是金黄色的,倒进锅里后,很快就热了,冒出淡淡的油烟,带着点油脂的香气。
陈师傅用筷子夹起一块毛豆腐,轻轻放进锅里,动作很轻,怕把菌丝碰掉。毛豆腐刚放进锅里,就传来“滋滋”的声音,油花轻轻溅起,一股浓郁的香气立刻飘了出来——比发酵时的香气更浓,里面混着油脂的焦香,还有菌丝被煎过的独特香气,闻起来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陆帆赶紧掏出相机,打开录像功能,拍下毛豆腐在锅里慢慢变化的过程。镜头里,毛豆腐的表面渐渐染上了的金黄色,菌丝被煎得微微卷曲,像一层酥脆的外壳,看起来格外有食欲。
“煎毛豆腐要小火慢煎,不能急,”陈师傅用筷子轻轻翻动毛豆腐,“先煎正面,煎到金黄色、酥脆,再翻过来煎反面,两面都煎好后,才能出锅。要是火太大,外面煎糊了,里面还没熟;火太小,又煎不出酥脆的口感。”
大概煎了五分钟,毛豆腐就煎好了。陈师傅把毛豆腐盛在一个白色的瓷盘里,瓷盘里还放了一片翠绿的生菜叶,用来垫底,看起来很清爽。“煎好的毛豆腐,要蘸着辣椒酱吃,这样才够味,”陈师傅从里屋拿出一个深红色的陶罐,里面装着自制的辣椒酱,“这是我自己做的辣椒酱,用的是本地山上种的小米辣,加上大蒜和生姜,剁碎了之后,用菜籽油慢慢炒香,再加上一点盐和糖,没有任何添加剂,吃起来香而不辣,能把毛豆腐的鲜味衬托得更突出。”
陈师傅舀出一勺辣椒酱,放在一个小瓷碟里,然后把瓷碟和装着毛豆腐的瓷盘一起端到陆帆面前。“快尝尝,刚煎好的,趁热吃才香,”陈师傅催促道,眼里带着期待的神情,像个等待被夸奖的孩子。
陆帆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毛豆腐。豆腐的表面金黄酥脆,轻轻一碰就能听到“咔嚓”的轻微声响,像是在咬薄脆的饼干。他咬了一口,首先尝到的是外皮的酥脆,带着点油脂的焦香,然后是内里的绵软——豆腐的口感很嫩,却不碎,带着点弹性,里面还能吃到细细的菌丝,没有一点怪味,反而增加了口感的层次。豆腐的清香和发酵后的微酸融合在一起,带着点稻草的清香,一点都不腻。
蘸上辣椒酱后,辣味适中,一点都不冲,反而把毛豆腐的鲜味衬托得更突出,还有大蒜和生姜的香味,在嘴里慢慢散开,和豆腐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再吃一块。“太好吃了!”陆帆忍不住赞叹,“外皮酥脆,里面绵软,还有淡淡的香味,一点都不像我想象中的样子。”
“很多人第一次吃毛豆腐,都觉得菌丝看起来怪,不敢下口,”陈师傅坐在对面的小凳上,看着陆帆吃得开心,自己也跟着笑了,“其实这菌丝才是毛豆腐的灵魂,没有菌丝,毛豆腐就没有这个味道了。我小时候第一次吃,也不敢吃,我爷爷就骗我说这是‘豆腐上的宝贝’,吃了能长个子,我才敢尝,一尝就爱上了。”
正说着,一个背着画板的年轻人推开了豆腐坊的门,探头探脑地往里看。陆帆抬头一看,竟然是昨天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大学生——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画板包,头发有点乱,脸上还带着点旅途的疲惫,手里拿着一支铅笔,笔尖还沾着点炭粉。“这么巧!你也来吃毛豆腐?”大学生看到陆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赶紧走进来,把画板放在墙边。
“我听张爷爷推荐的,说陈师傅的毛豆腐做得最好,”陆帆笑着说,“你怎么也知道这里?”
“我去年来黄山写生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这家豆腐坊,”大学生拿起一块毛豆腐,放进嘴里,眼睛立刻亮了,“陈师傅的毛豆腐是汤口最好吃的,比景区里那些卖游客的好吃多了。景区里的毛豆腐,要么煎得太老,要么没发酵好,一点都不香。”
陈师傅笑着从锅里又煎了几块毛豆腐,盛在另一个瓷盘里,递给大学生,又倒了两杯豆浆:“你们年轻人都喜欢吃新鲜的东西,能喜欢我做的毛豆腐,我很高兴。”他看着手里的毛豆腐,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就是现在愿意学这门手艺的年轻人太少了。我儿子在合肥工作,做的是IT,每次我让他回来学做毛豆腐,他都不愿意,说又累又不赚钱,不如在城里上班舒服。我怕等我做不动了,这门手艺就没人传了。”
陆帆心里一动,掏出随身的牛皮纸笔记本——封面己经被磨得有些毛边,里面记满了他这一路的见闻和感受。他翻开新的一页,拿起钢笔,在上面写道:“毛豆腐的发酵,是徽州人对时间的尊重,对食材的敬畏。一块小小的豆腐,要经过选豆、泡豆、磨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发酵、煎制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每一步都需要耐心。这背后,是几代人的坚守和传承,是在艰苦环境中对美味的追求。在这个追求快节奏、追求效率的时代,这样的坚守,更显得珍贵。”
大学生也放下筷子,认真地看着陈师傅,说:“陈师傅,我这次来黄山,本来是想画黄山的风景,看到您做毛豆腐的过程,我忽然觉得,您的手艺比黄山的风景更值得画。我想把您做毛豆腐的每一个步骤都画下来,做成一本画册,让更多人知道这门手艺,知道毛豆腐背后的故事,您愿意吗?”
陈师傅愣了一下,手里的木勺停在半空中,眼睛里渐渐泛起了泪光。他赶紧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声音有点沙哑:“愿意!当然愿意!我做了一辈子毛豆腐,从来没想过有人会把我做豆腐的过程画下来。能让更多人知道毛豆腐,知道我们徽州的手艺,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陆帆跟着陈师傅,详细记录下毛豆腐制作的每一个步骤。他用相机拍下陈师傅泡豆时专注的神情,拍下他转动石磨时用力的样子,拍下他点卤时小心翼翼的手势,拍下他检查发酵房时认真的眼神。他还拿出笔记本,记下每一个步骤的要点:选豆要选本地黄豆,泡豆要换三次水,磨浆要用石磨,点卤要慢要匀,发酵温度要控制在二十二度左右……
陈师傅也打开了话匣子,跟陆帆聊了很多关于徽州饮食文化的故事。他说,以前徽州人家家户户都会做毛豆腐,每到冬天,院子里都会摆着几个发酵毛豆腐的木盒,整个村子都飘着毛豆腐的香气;他说,毛豆腐最好的搭配是臭鳜鱼,一个鲜,一个香,放在一起吃,味道能翻倍;他说,以前徽商出去做生意,都会带几块晒干的毛豆腐,饿了就拿出来煎一煎,既能填肚子,又能解乡愁,就像带着家乡的味道在身边。
中午的时候,陈师傅留陆帆和大学生在豆腐坊吃饭。他从里屋拿出一块五花肉,是本地土猪的肉,肥瘦相间,颜色是深红色的。他把五花肉切成小块,放进锅里炒出油脂,然后加入姜片、葱段、酱油,炒出香味,再把几块发酵好的毛豆腐放进锅里,加水慢慢炖。“这是我奶奶传下来的做法,叫毛豆腐烧肉,”陈师傅一边炖,一边说,“以前家里来了客人,才会做这道菜,算是招待客人的硬菜。毛豆腐吸了肉的油香,会变得更绵软,肉也因为毛豆腐的加入,变得不那么油腻,特别下饭。”
炖了大概二十分钟,毛豆腐烧肉就做好了。盛在一个青花瓷碗里,五花肉是深红色的,毛豆腐是淡黄色的,汤汁是深褐色的,看起来格外有食欲。陆帆尝了一口,五花肉炖得很烂,入口即化,油脂都被毛豆腐吸走了,一点都不腻;毛豆腐吸满了肉的油香,变得更绵软,咬一口,里面的汤汁就流出来,满是肉香和豆香,用来拌米饭,好吃得让人忍不住多吃一碗。
“太香了!”大学生一边扒米饭,一边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腐烧肉,以后我要是想念这个味道了,还来您这里吃。”
“随时来,”陈师傅笑得很开心,“只要我还在做毛豆腐,你们来,我就给你们做。”
吃完饭,陆帆准备离开,要去屯溪老街——陈师傅说,屯溪老街有更老的毛豆腐字号,还有很多徽州的传统小吃,比如黄山烧饼、徽州挞馃,值得去看看。陈师傅从里屋拿出一个陶罐,是浅褐色的,上面刻着简单的花纹,里面装着几块发酵好的毛豆腐,又拿出一个军绿色的水壶,装满了刚煮好的豆浆。“这个陶罐是我年轻时用的,现在给你装毛豆腐,路上要是想吃了,就找个地方煎一煎,”陈师傅把陶罐和水壶递给陆帆,又拍了拍他的肩膀,“屯溪老街的‘老街第一楼’,毛豆腐也做得不错,你可以去尝尝,对比一下,看看哪家的更好吃。要是以后再来黄山,记得来我这里,我给你做毛豆腐烧肉。”
陆帆接过陶罐和水壶,手里沉甸甸的,心里也暖暖的。他说了声“谢谢”,又和大学生道别——大学生要留在豆腐坊,画陈师傅做毛豆腐的过程,才背着背包,慢慢走出豆腐坊。
走在回客栈的路上,小溪的水依旧清澈,老樟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像撒了一把碎金。陆帆看着手里的陶罐,想起陈师傅转动石磨时用力的样子,想起他点卤时小心翼翼的手势,想起他说起手艺传承时担忧的眼神,心里充满了感动。他掏出手机,打开剪辑软件,把今天拍的毛豆腐制作过程剪成了一段短视频,配了一段文字:“黄山脚下的毛豆腐,是徽州人用时间和耐心酿出的美味。从一颗黄豆到一块长满菌丝的毛豆腐,要经过八道工序,要等三天时间。这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几代人的坚守,是对传统手艺的敬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下来,才能尝到最本真的味道。”
视频发出去没多久,就有很多粉丝评论:“原来毛豆腐是这样做的!看起来好复杂,难怪这么好吃!”“陈师傅好厉害,一辈子坚守一门手艺,太不容易了!”“下次去黄山,一定要去陈师傅的豆腐坊尝尝,支持传统手艺!”“陆帆能不能多拍点这样的视频,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快要消失的手艺!”
陆帆看着评论,心里忽然觉得,自己的旅程不仅仅是记录美食,更是在记录那些即将被遗忘的传统手艺,记录那些坚守在传统里的普通人。他想起在连云港遇到的李老板,想起他凌晨去码头接渔船、认真挑选每一只梭子蟹的样子;想起在徐州遇到的周老板,想起他给客人装羊肉干时,特意撒上芝麻、说“能提香”的样子;想起现在的陈师傅和汪阿姨,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却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味道,传承着一种文化的记忆。
回到客栈,陆帆收拾了行李——他的背包里装着陈师傅给的毛豆腐和豆浆,装着汪阿姨送的黄山毛峰,还装着这一路记录的笔记本和相机。张爷爷帮他把行李搬到门口,手里还拿着一个纸包,里面装着几块黄山烧饼:“这是我自己做的,你路上吃,垫垫肚子。屯溪老街人多,你去了之后,记得多逛逛,那里的徽州挞馃也好吃,是用梅干菜和肉做的,外皮酥脆,里面香。”
“谢谢您,张爷爷,”陆帆接过纸包,里面的烧饼还带着温热的温度,“等我从屯溪回来,再跟您聊黄山的故事。”
陆帆背着背包,手里提着陈师傅给的陶罐,沿着青石板路慢慢离开汤口镇。远处的黄山依旧被薄雾笼罩,山顶的云慢慢流动,像一幅动态的水墨画,随着风的方向不断变化着形状。他回头望了一眼,汤口镇的白墙黛瓦在雾里若隐若现,陈师傅的豆腐坊门口,那棵老樟树依旧像一把巨大的绿伞,静静地守护着这个小小的镇子,守护着毛豆腐的味道,守护着徽州的传承。
“下一站,屯溪老街,”陆帆在心里默念,“去寻找更多徽州的味道,去记录更多关于传承的故事。”他握紧手里的陶罐,脚步坚定地向前走,阳光透过薄雾洒在他身上,温暖而明亮,像在为他的旅程祝福,也像在为那些坚守传统的手艺人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