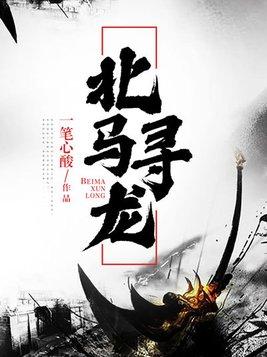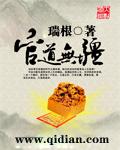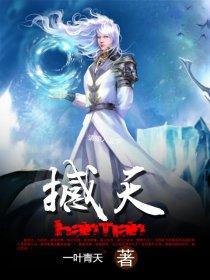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在哪里查找 > 第44章 龙泉瓷韵黄粿里的山海匠心(第1页)
第44章 龙泉瓷韵黄粿里的山海匠心(第1页)
陆帆在景宁民宿的晨光里醒来时,窗纱被风掀起一角,漏进的光线里浮着细小的尘埃。窗台上的野蔷薇沾着三两颗露珠,最大的那颗悬在花瓣尖上,折射着晨光,像颗碎钻——那是昨晚蓝晓雨临走前踮着脚放的,她当时还特意把花瓣捋顺,说“让它陪你醒来看景宁的早晨,比闹钟温柔”。
陆帆伸手碰了碰露珠,凉意顺着指尖漫上来,像昨晚蓝晓雨递来的那杯敕木山绿茶,清清爽爽的,还带着点草木的淡香。他坐起身,目光落在床边的帆布背包上:蓝奶奶给的乌饭叶干用牛皮纸包着,纸角被浆糊糊得整整齐齐,凑近能闻到淡淡的草木香;王爷爷给的草药茶装在粗陶小罐里,罐口用红布扎着,布上还绣着个小小的“药”字;笔记本里夹着蓝晓雨画的简易龙泉地图,纸是小学生用的方格本撕下来的,边缘还带着点毛糙,上面用蓝色铅笔标着“老吴青瓷工作室”,旁边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瓷碗,碗沿写着“找吴叔,他懂瓷也懂吃,能带你吃最香的黄粿”。
“陆帆哥哥,这是我表舅吴叔的电话,你记好了,他手机号最后三位是189,别打错啦。”昨晚蓝晓雨送他到民宿楼下时,把写着号码的纸条塞进他手心,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的,背面还有半道数学题,“吴叔在龙泉做青瓷几十年了,去年我去他那儿学过半个月拉坯,他教我捏小瓷碗,我捏坏了十几个才成。对了,龙泉的黄粿和我们景宁的不一样,我们用糯米,他们用高山粳米,蒸透了用石臼捶,捶得越久越Q,蘸着红糖吃,甜到心里去,你一定要试试!”
此刻陆帆站在景宁汽车站的站牌下,手里捏着那张纸条,指腹把号码都摸得有点发皱。晨雾还没散,远处的敕木山藏在白蒙蒙里,山尖偶尔露出来一点,像浮在云里的青黛。去龙泉的班车停在站台边,车身印着“丽水文旅——龙泉青瓷专线”,绿色的车身上画着缠枝莲纹,和他在蓝晓雨家看到的畲族织布纹样有点像,车头上摆着个巴掌大的青瓷花瓶,里面插着两枝野蔷薇,花瓣上也沾着露珠,和他窗台上的那枝一模一样。
“小伙子,去龙泉看瓷啊?”卖早点的阿姨推着小车从旁边经过,车轱辘压在青石板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小车的蒸笼冒着白汽,飘着糯米的甜香,笼屉是竹编的,边缘磨得发亮,“来个麻糍?景宁的麻糍,用的是今年的新糯米,蘸芝麻糖,热乎着呢!”
陆帆买了两个,阿姨用油纸包好递给他,油纸还带着点蒸笼的温度。他咬了一口,糯米的黏软裹着芝麻的香,还有点红糖的甜,嚼的时候能感觉到米粒的细腻——浙南的吃食,好像都带着点土地的温软,从缙云的烧饼到景宁的乌米饭,再到这麻糍,都让人想起灶台上的烟火气。
“阿姨,您去过龙泉吗?龙泉的黄粿真的比景宁的好吃吗?”陆帆一边嚼一边问。
“去过去过!”阿姨笑着擦了擦手,手上沾着点糯米粉,“去年我去龙泉走亲戚,吃了他们的黄粿,那叫一个Q!用石臼捶的,捶得能拉出丝来,蘸着红糖吃,比我做的麻糍还甜。对了,你去龙泉,一定要去巷口那家阿婆的黄粿店,阿婆姓周,做黄粿几十年了,她的石臼还是她婆婆传下来的,有五十多年了!”
班车缓缓驶出景宁,山路蜿蜒,车窗外的风景慢慢变了——畲乡的蓝色小楼变成了成片的竹林,竹子是毛竹,长得又高又首,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来,在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撒了一地碎金。偶尔能看到溪边的水车,木头的辐条己经有点发黑,吱呀吱呀转着,把溪水泼成碎银,落在石头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司机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龙泉人,头发里掺着点白,穿着蓝色的工装褂子,褂子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胳膊。他操着带点方言的普通话,时不时跟乘客搭话:“前面就是小梅镇,再过半小时就到龙泉市区了。你们去龙泉,一定要去青瓷博物馆看看,还有大窑遗址,那可是宋代的窑址,能看到老瓷片!吃的嘛,黄粿、溪鱼、笋干烧肉,一样都不能少,不然等于白来!”
“师傅,龙泉的黄粿为什么要用粳米啊?糯米不是更黏吗?”陆帆凑到前排,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麻糍。
“那当然有讲究!”师傅一拍方向盘,声音都亮了,眼睛里闪着光,“我们龙泉的高山粳米,日照足,颗粒,蒸出来自带甜味,捶出来的黄粿不粘牙,有嚼劲。要是用糯米,黏得能粘住牙,吃两口就腻了。我们吃黄粿,要么蘸红糖,要么配咸菜肉末,早上吃一碗,扛饿,上山干活都有力气!”
师傅说着,从仪表盘里摸出个油纸包,打开是切成小块的黄粿,颜色是淡黄色的,看着就很有弹性。“你尝尝,这是我老婆子昨天刚做的,凉了也好吃,你试试。”
陆帆接过一块,放在嘴里嚼了嚼,果然不粘牙,米香很浓,带着点淡淡的清甜,嚼到最后还有点韧劲,比他以前吃的年糕更有嚼头。“好吃!比我以前吃的年糕更Q!”
“那是!”师傅得意地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了一团,“我们龙泉人做黄粿,讲究‘三蒸三捶’。粳米要提前泡三个小时,泡到手指能捏碎才行;第一次蒸到半熟,拿出来晾一会儿,再蒸第二次,蒸到米粒开花;第三次蒸透,才能放进石臼捶。捶的时候要两个人配合,一个人捶,一个人翻,捶足半个钟头,捶到米团能拉出丝来,这样做出来的黄粿才够劲!”
班车驶进龙泉市区时,陆帆一眼就看到了路边的青瓷雕塑——那是个三米多高的青瓷花瓶,瓶身上刻着龙泉窑经典的梅子青釉,阳光照在上面,釉色像雨后的青山,温润得能滴出水来。花瓶的颈部刻着缠枝莲纹,花瓣的纹路清晰可见,连花芯的细节都做得很精致。
车站门口的宣传栏是不锈钢框架的,上面贴着“中国青瓷小镇——龙泉”的海报,海报上有个穿着汉服的姑娘,手里捧着个青瓷碗,碗里装着黄粿,配着“千年瓷韵,一口黄粿,品龙泉味道”的标语。旁边还有张照片,是大窑遗址的龙窑,依山而建,像一条卧在山里的巨龙。
陆帆按着蓝晓雨给的地址,在车站门口打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姓叶,戴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很亮,车里放着龙泉本地的山歌,歌词是“青瓷白,黄粿甜,龙泉山水养神仙,溪水清,竹林密,瓷香飘满千万里……”
“哥,你是来旅游的吧?看你背着背包,还拿着地图。”小叶师傅一边开车一边问,方向盘上挂着个小小的青瓷平安符,符上刻着个“安”字。
“是啊,去老吴青瓷工作室,找吴叔。”陆帆说。
“吴叔?是不是吴明海吴叔?”小叶师傅眼睛一亮,“他可是我们龙泉的青瓷老匠人!去年他做的梅子青釉花瓶,在省里的陶瓷展上还拿了奖呢!我小时候还去他工作室玩过,他教我捏过小瓷狗,我捏得歪歪扭扭的,他还夸我有天赋。”
小叶师傅的车开得很稳,沿着剑川大道往古城方向走。路边的店铺很多都和青瓷有关,有的卖青瓷餐具,有的卖青瓷饰品,还有的卖青瓷茶具,橱窗里摆着的青瓷碗、青瓷瓶,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偶尔能看到卖黄粿的小店,门口摆着石臼和木槌,有的还冒着热气,飘着米香。
“吴叔不仅懂瓷,还懂吃。”小叶师傅说,“他知道哪家的黄粿最地道,哪家的溪鱼最新鲜,哪家的笋干烧肉最香。你跟着他,肯定能吃到最正宗的龙泉味道。对了,你吃过龙泉的溪鱼吗?就是石斑鱼,很小,但是很鲜,蒸着吃最好吃,不用放太多调料,就放点盐和姜丝,鲜得能掉眉毛!”
工作室在龙泉古城的巷子里,巷子叫“青瓷巷”,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很光滑,路边的墙面上画着青瓷制作的流程,从揉瓷土到拉坯,再到上釉、烧制,每一步都画得很细致。巷子口有个老槐树,树干很粗,需要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树枝上挂着红灯笼,灯笼上写着“青瓷巷”三个字。
老吴的工作室是一栋白墙黑瓦的老房子,门口挂着块木制的招牌,上面写着“吴记青瓷”,字是手写的,苍劲有力,招牌边缘用铜皮包着,防止磨损。木牌旁边摆着两个青瓷花盆,里面种着兰草,叶片上还沾着水珠,花盆的釉色是粉青的,看着很温润。
陆帆推开门时,听到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像有人在用小锤子敲瓷器,声音清脆,在巷子里都能听到。
“有人吗?”陆帆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手里还捏着蓝晓雨写的纸条。
声音停了,一个穿着灰色工装的中年男人从里屋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个小锤子,锤子头是铜的,闪着光。男人个子不高,大概一米六左右,肩膀很宽,显得很结实,脸上沾着点白色的瓷土,像不小心蹭上去的,眼睛很亮,像龙泉溪里的水,透着清透。
“你是?”男人看着陆帆,语气很温和。
“吴叔您好,我是蓝晓雨的朋友,叫陆帆,从景宁过来的,晓雨让我找您。”陆帆把蓝晓雨写的纸条递过去,纸条被他攥得有点皱了。
老吴接过纸条,眯着眼睛看了看,眉头慢慢舒展开来,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拍了拍陆帆的肩膀,手心很粗糙,带着点瓷土的颗粒感:“哦!晓雨啊,我想起来了,去年她还来我这儿学过半个月拉坯呢,那丫头手巧,学了没几天就能捏出像样的小瓷碗了。快进来,外面冷,刚在修一个瓷碗,没听见你敲门。”
陆帆跟着老吴走进屋里,一股淡淡的瓷土香扑面而来,混合着点草木灰的味道。工作室分前后两部分,前面是展示区,后面是作坊。展示区的架子上摆着很多青瓷作品,有的是花瓶,有的是碗,有的是盘子,还有些小摆件,比如青瓷做的小兔子、小松鼠,憨态可掬。架子是松木做的,刷着清漆,能看到木头的纹理。
靠窗的位置放着个拉坯机,是电动的,机身是银色的,旁边堆着几袋瓷土,袋子上印着“龙泉优质瓷土”的字样,地上放着个大木桶,里面泡着瓷土,水面上飘着层薄薄的泡沫。“这是我的工作室,前面是展示区,后面是作坊,我和我儿子吴磊一起做瓷,他今天一早去山里拉瓷土了,晚点才能回来。”老吴一边说,一边从架子上拿了个青瓷杯,给陆帆倒了杯茶。
茶杯是粉青釉的,杯壁很薄,大概只有两毫米厚,透过杯子能看到茶水的颜色,像淡绿色的玉。“这杯子是我去年做的,用的是龙泉本地的瓷土和釉石,你尝尝茶,是凤阳山的高山云雾茶,今年的新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