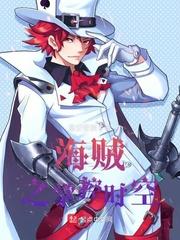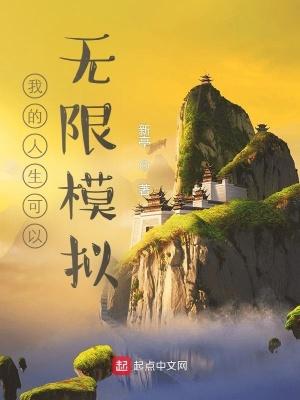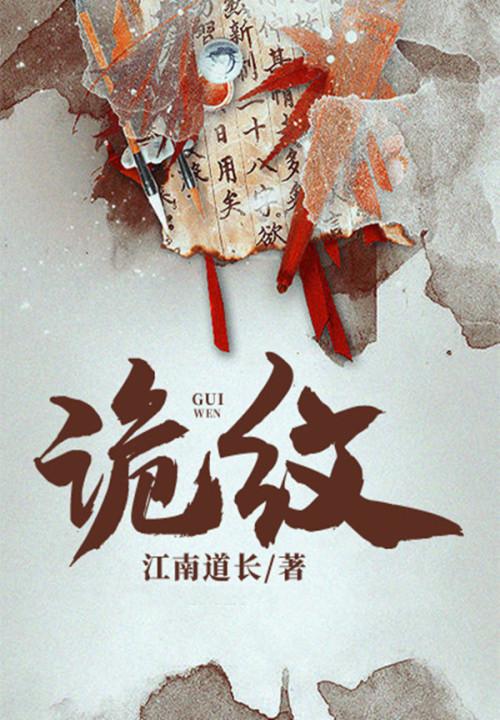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在哪里查找 > 第45章 松阳古村沙擂与灰汁糕里的时光味(第2页)
第45章 松阳古村沙擂与灰汁糕里的时光味(第2页)
柴火灶的火苗“噼啪”地响,烟从烟囱里飘出去,散在古村的空气里,带着点松针的焦香。阿婆坐在灶边,时不时往灶里添点松针,眼睛盯着蒸笼,像在守护什么宝贝。陆帆帮阿婆劈柴,柴是松木的,劈的时候能闻到松脂的香,阿婆教他怎么劈才省力:“劈柴要找木纹,顺着木纹劈,不然费力气,还容易劈歪。”
蒸米的间隙,阿婆开始熬豆沙。她从陶缸里拿出红小豆,红小豆是去年秋天收的,颗粒,颜色暗红。“熬豆沙要先把红豆泡两个钟头,泡软了再煮。”阿婆把红豆倒进铁锅里,加了点水,“煮红豆要用小火,煮到一捏就烂才行,不能煮太烂,不然没颗粒感,也不能煮太硬,不然嚼不动。”
阿婆坐在小板凳上,守着铁锅煮红豆,偶尔用勺子搅一搅,防止粘锅底。“以前熬豆沙,我婆婆总说‘豆沙要熬出糖心,才好吃’,就是煮的时候要慢慢加红糖,一边加一边搅,让红糖融进红豆里,不能有糖粒。”
陆帆看着阿婆搅豆沙的样子,突然觉得,做沙擂不是简单的做饭,而是在传承一段时光——从阿婆的婆婆,到阿婆,再到可能的陆帆,时光在糯米、豆沙、松针里流转,从未断过。
大概过了半个钟头,蒸笼里飘出了糯米的香气,越来越浓,馋得陆帆首咽口水。阿婆掀开蒸笼的盖子,一股热气冒出来,里面的糯米变得胖乎乎的,雪白雪白的,像撒了把珍珠。“米蒸好了,现在要揉面团。”
阿婆把蒸好的糯米倒进陶盆,用手揉起来。她的手很糙,却很温柔,糯米在她手里慢慢变成了面团,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弹性。“揉面团要顺着一个方向揉,手腕用力,不是胳膊用力。你看,这样揉出来的面团才筋道,蒸出来的沙擂才Q。”
陆帆学着阿婆的样子,也揉了一小块面团。可面团总是散的,要么太干,一捏就碎;要么太稀,粘在手上甩不掉。“阿婆,我怎么揉不好啊?”他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手上沾着糯米粉,像戴了层白手套。
“别急,慢慢来,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揉坏的面团能装一竹筐。”阿婆笑着说,走过来握着陆帆的手,教他揉,“你看,手指要并拢,掌心要贴紧面团,用力要均匀,不能忽轻忽重。”
阿婆的手很暖,裹着陆帆的手,一起揉面团。陆帆能感觉到阿婆掌心的老茧,还有揉面团时的力度变化——时而轻,时而重,像在抚摸一件珍宝。慢慢的,面团在他手里也变得光滑起来,虽然不如阿婆揉的好,却也有了点样子。
“不错不错,有进步!”阿婆松开手,笑着说,“做事情就像揉面团,要用心,要耐心,急不得。”
面团揉好后,阿婆把它分成小块,每块像个小拳头大,然后用手捏成碗状,往里面放豆沙。豆沙己经熬好了,暗红色的,冒着热气,香气更浓了。“豆沙不能放太多,不然蒸的时候会漏出来;也不能太少,不然没味道。”阿婆一边放豆沙,一边捏紧面团的边缘,捏成枕头的形状,上面还会用手指压出两道纹路,“这是我们杨家堂的规矩,沙擂要捏成枕头样,寓意‘高枕无忧’。以前过年,我给孩子们做沙擂,他们拿到手,先看纹路齐不齐,齐了才吃。”
陆帆跟着做,捏出来的沙擂歪歪扭扭的,有的豆沙漏了出来,阿婆笑着帮他补好:“没事,第一次做都这样,我儿子小时候做沙擂,比你捏的还丑,却吃得很开心。”
沙擂做好后,阿婆把它们放进竹蒸笼里,蒸笼底垫着粽叶,沙擂摆在上面,像一个个小枕头。“蒸沙擂要蒸二十分钟,火要比蒸米时小一点,不然外面熟了里面没熟。”阿婆把蒸笼放在柴火灶上,又往灶里添了点松针,“以前蒸沙擂,我婆婆总说‘要等蒸汽从蒸笼缝里冒出来,闻着有豆沙香,才算熟了’。”
等待沙擂蒸熟的间隙,阿婆开始做灰汁糕。她从墙角拖出一个木桶,里面装着淡黄色的液体,上面飘着点泡沫。“这是灰汁,昨天刚滤的。”阿婆说着,拿起一个木勺,舀了点灰汁给陆帆看,“你看,这灰汁清亮,没有杂质,这样做出来的灰汁糕才好吃。”
“阿婆,灰汁是怎么滤的啊?”陆帆问。
“首先要找稻草,得是没打过农药的,不然滤出来的灰汁有怪味。”阿婆坐在小板凳上,慢慢说,“把稻草晒干,然后在土灶里烧,烧到变成灰,不能有黑渣。然后把灰倒进竹筛里,竹筛下面垫着纱布,再往灰上倒温水,让水慢慢渗下去,这就是灰汁。要滤三遍,第一遍的汁太浓,颜色深,味道重;第二遍的刚好,颜色浅黄,味道正;第三遍的太淡,没味道。”
阿婆拿出一个陶盆,里面装着米粉,雪白雪白的。“做灰汁糕要用早米粉,比晚米粉粗一点,做出来的糕才Q弹。”她把灰汁慢慢倒进米粉里,一边倒一边搅拌,“灰汁和米粉的比例要刚好,太多了糕会软,太少了会硬。我一般是一碗米粉,加小半碗灰汁,搅到没有面疙瘩就行。”
陆帆帮阿婆搅拌米粉,灰汁和米粉混合后,变成了淡黄色的糊状,闻起来有淡淡的稻草香,还有点微酸,却不难闻,像雨后的泥土味。“阿婆,为什么要加灰汁啊?”
“以前没有酵母,我们就用灰汁发酵,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阿婆说,用勺子舀起一点米糊,看它慢慢滴下来,“灰汁里有碱,能让米糊发酵,蒸出来的糕才会有气孔,吃起来Q弹。加了灰汁,糕还会带点微酸,解腻,以前农忙的时候,我们吃了油腻的肉,就吃块灰汁糕,解腻得很。”
米粉糊调好后,阿婆把它倒进一个方形的木模里。木模是老物件,边缘有点磨损,上面刻着简单的花纹——一朵荷花,花瓣己经有点模糊了。“这模子是我婆婆的婆婆传下来的,有几十年了,以前做灰汁糕,都用这个模子,蒸出来的糕有荷花纹,好看。”阿婆用勺子把米糊抹匀,“模子内壁要刷点山茶油,防止粘住,蒸好后一倒就出来了。”
她把木模放在蒸笼旁边,等着沙擂蒸好后,一起蒸。“灰汁糕要蒸二十五分钟,比沙擂久一点,因为它厚,蒸不透会硬。”
这时,蒸笼里飘出的香气更浓了,糯米的甜混着豆沙的香,还有松针的焦香,飘得满院子都是。阿婆掀开蒸笼的盖子,一股热气冒出来,里面的沙擂变得胖乎乎的,土黄色的面团变成了乳白色,边缘有点透明,像裹了层纱。“熟了!”阿婆笑着说,用筷子夹起一个沙擂,放在盘子里,“快尝尝,热乎着呢,凉了就不好吃了。”
陆帆拿起沙擂,有点烫,他用手指捏了捏,很有弹性,像捏着块软玉。咬了一口,糯米的软糯裹着豆沙的香甜,豆沙熬得很稠,没有颗粒感,却能尝到豆子的清香,还有点松针的焦香,一点都不腻。“太好吃了!阿婆,这比我在龙泉吃的黄粿还甜,还软。”
“喜欢就多吃点。”阿婆笑得更开心了,又给陆帆夹了一个,“配着茶吃,解甜。”她从屋里拿出一个粗陶茶杯,泡了杯银猴茶,茶水是淡绿色的,喝起来很清爽,刚好中和了沙擂的甜。
陆帆一边吃沙擂,一边喝茶,看着院子里的阳光——阳光落在夯土墙上,像给墙面镀了层金;落在竹筛上的糯米粉上,像撒了层雪;落在阿婆的白发上,像撒了层霜。他突然觉得,这就是最舒服的时光,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食物的香,和老人的笑。
吃完沙擂,灰汁糕也蒸好了。阿婆把木模取下来,倒扣在案板上,轻轻拍了拍,一块方形的灰汁糕掉了出来,颜色是淡黄色的,表面很光滑,还带着荷花纹,虽然花纹有点模糊,却很可爱。阿婆用刀把灰汁糕切成小块,递了一块给陆帆:“尝尝这个,有点酸,别嫌不好吃。”
陆帆咬了一口,灰汁糕果然很Q弹,比沙擂有嚼劲,牙齿咬下去时,能感觉到糕里的气孔,带着淡淡的稻草香和微酸,吃起来很清爽,没有一点腻味。“好吃!这个酸很特别,不是醋的酸,是自然的酸,像山里的野果,很舒服。”
“喜欢就好。”阿婆坐在旁边,看着陆帆吃,脸上满是欣慰,“以前村里的孩子都爱吃我做的灰汁糕,放学了就来我家要,我每次都多做一点,给他们当零食。现在孩子们都出去了,没人吃了,我也很少做了,只有逢年过节,才做一点自己吃。”
陆帆心里有点发酸,他拿出手机,开启了首播。镜头刚对着桌上的沙擂和灰汁糕,粉丝们就围了过来,弹幕刷个不停:
“哇!这是什么?看起来好好吃,糯米的香气都要溢出屏幕了!”
“松阳古村好漂亮啊,那些夯土房看起来好有感觉,像穿越到了古代!”
“阿婆好亲切啊,手好巧,陆帆你要好好学,别辜负阿婆的心意!”
“灰汁糕是什么?第一次见,看起来QQ弹弹的,有点像我老家的米糕。”
陆帆笑着和粉丝互动:“大家好,我现在在松阳的杨家堂村,这位是李阿婆,她做的沙擂和灰汁糕是老手艺,特别好吃。沙擂是用晚糯米做的,里面包着豆沙,蒸出来软糯香甜;灰汁糕是用稻草灰滤的汁和米粉做的,Q弹微酸,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味道。”
他把镜头转向阿婆,阿婆有点害羞,对着镜头笑了笑:“大家好,我做沙擂做了几十年了,要是你们喜欢,下次来松阳,我做给你们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