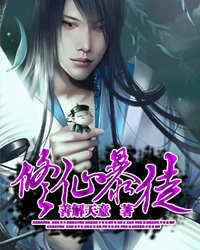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在哪里查找 > 第58章 泰州靖江蟹黄汤包一口入魂的江鲜(第2页)
第58章 泰州靖江蟹黄汤包一口入魂的江鲜(第2页)
陆帆学着周老板的样子,用筷子轻轻夹起一个汤包。他特意夹在褶子的地方,因为周老板说那里皮厚,不容易破。汤包的皮很软,夹起来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的汤在晃动,像抱着一个小小的热水袋。他小心翼翼地把汤包移到自己的碟子里,碟子里己经倒好了姜丝醋,姜丝切得很细,像一根根雪白的针,浮在醋上面,还撒了点葱花,看起来很清爽。
他用筷子在汤包的顶部偏下一点的位置轻轻戳了一个小口——周老板说这个位置戳口,汤汁不容易溅出来。瞬间,一股滚烫的汤汁涌了出来,带着蟹的鲜和肉的香,还有皮冻的醇厚,热气裹着香味飘到鼻尖,让他忍不住眯起了眼睛。他赶紧拿起勺子,小心地接着流出来的汤,汤是橙黄色的,里面还飘着点细小的蟹肉颗粒,看起来很浓稠。
他吹了吹勺子里的汤,然后抿了一口。汤刚入口时有点烫,慢慢咽下去,鲜美的味道就在嘴里散开了——蟹黄的香很浓郁,却一点都不腥,带着点淡淡的油香;蟹肉的颗粒感很明显,咬起来有嚼劲;肉的鲜很醇厚,和蟹的鲜完美融合在一起;皮冻化成的汤很滑,顺着喉咙滑下去,暖到胃里,连带着刚才在江风里受的凉都消散了。“太鲜了!”陆帆忍不住赞叹,又喝了一口汤,这次他特意蘸了点姜丝醋,醋的酸和姜丝的辣刚好中和了蟹的油腻,让汤的鲜更突出了,一点都不觉得腻。
喝完汤,他才开始吃汤包的皮和馅。皮很薄,却很有韧劲,咬起来不会碎,还带着点面粉的甜,吸了汤的皮更软了,入口即化。馅里的蟹肉很多,每一口都能吃到大块的蟹肉,和鲜肉拌在一起,鲜而不腻,鲜肉的肥瘦比例刚好,不会太柴,也不会太油。他吃了一个,还想再吃,却想起周老板说的“慢慢吃”,只好放慢速度,小口小口地品。
周老板坐在旁边的桌子旁,看着他吃,笑着问:“怎么样?和扬州的蟹黄汤包比,不一样吧?扬州的汤包我也吃过,更小巧,汤少一点,蟹黄味没这么浓,我们靖江的汤包更大,汤多,蟹黄味更足,吃着更过瘾。”
陆帆点点头,嘴里还嚼着汤包,含糊地说:“不一样!您家的汤包更鲜,蟹肉更多,汤也更浓,太好吃了!”周老板听了,笑得更开心了,给陆帆添了碗大麦粥:“再喝点粥,垫垫肚子,大麦粥是用本地的大麦熬的,熬了一个小时,加了点盐,清淡,解腻。我爹以前总说,吃汤包配大麦粥,才是正经吃法,不然吃多了容易腻。”
陆帆接过粥碗,粥是淡绿色的,熬得很稠,用勺子舀起来,能挂在勺子上,不会马上掉下来。他喝了一口,粥的清淡刚好解了汤包的油腻,还带着点大麦的清香,很好喝。他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人,正在包汤包,老人的动作和刘师傅很像,都是捏着十八道褶。“周叔,这是您爹吧?”他问。
“对,是我爹,”周老板的眼神里带着点怀念,“这张照片是我爹五十岁的时候拍的,那时候他还在城头港码头摆摊,用的是铁皮蒸笼,不像现在用竹编的。那时候条件差,摆摊的地方没有棚子,夏天晒得慌,冬天冷得很,我爹就用一块塑料布搭个棚子,照样卖汤包。”
他顿了顿,继续说:“我年轻时不想继承汤包店,觉得卖汤包太累,去外地打工,在工厂里做流水线,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累得要死,还赚不到多少钱。后来我爹生病,没人看店,我才回来接手。刚开始手生,擀皮总擀不圆,捏褶子总断,我爹就坐在旁边教我,说‘心要静,手要稳,做汤包和做人一样,急不得’。我练了三个月,才把擀皮和捏褶子练会,现在我爹不在了,我每天开店前都会给他的照片上一炷香,告诉他今天的汤包卖得很好,没给他丢脸。”
陆帆听得心里暖暖的,拿出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下“靖江蟹黄汤包”,然后画了一个圆鼓鼓的汤包,旁边标注:“长江中华绒螯蟹(三两以上雌蟹),手工擀皮(高筋面粉+30度温水+猪油,醒面3小时,厚度0。5毫米),十八道褶,皮冻(猪脊皮熬3小时),配姜丝醋(去寒提鲜),鲜、香、肥、美”。他还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蒸笼,上面写着“老季家”三个字。
旁边桌的老奶奶听到他们的对话,笑着转过头。老奶奶穿着灰色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个黑色的发夹固定住,戴着一副银色的老花镜,面前的蒸笼里还剩两个汤包。“小伙子是第一次来靖江吃汤包吧?”老奶奶的声音很温和,带着点泰州口音,“老季家的汤包我吃了二十年了,从周老板他爹摆摊的时候就吃,味道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鲜。”
她拿起一个汤包,熟练地捏着褶子的地方,轻轻提起来,慢慢移到碟子里,用筷子戳了个小口,然后拿起勺子喝汤,动作很优雅,一看就是常来吃的。“我年轻的时候,我老伴是码头的搬运工,每次扛完货,都会去周老板他爹的摊子上买一笼汤包,坐在江边吃,等我下班,然后分我一半。他总说,‘这汤包鲜,你吃了能解乏’。”老奶奶的眼里闪过一丝温柔,“现在他不在了,我每个月都来吃一次,都会坐在以前他常坐的位置,点一笼汤包,放两副筷子,仿佛他还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吃汤包。”
陆帆听得鼻子有点酸,他给老奶奶添了点姜丝醋,说:“奶奶,您慢慢吃,不够我再给您点一笼。”老奶奶摇摇头,笑着说:“不用啦,我年纪大了,吃一笼就够了,多了消化不了。小伙子,你知道靖江的蟹黄汤包和别的地方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苏州的小笼包。”
陆帆摇摇头,说:“不知道,您给我讲讲吧。”
“不一样,差远了!”老奶奶放下勺子,认真地说,“苏州的小笼包是甜口的,肉馅多,蟹肉少,汤也少,吃起来像吃肉包子,没什么蟹味。我们靖江的汤包是咸鲜口的,蟹肉多,汤多,吃的就是蟹的鲜,一口汤下去,满嘴都是蟹香,那才叫吃汤包。还有,我们的汤包皮更薄,能看到里面的汤,苏州的小笼包皮厚一点,看不到里面的馅,吃起来没那么有盼头。”
她指着自己的碟子里的姜丝醋,继续说:“我们吃汤包必须配姜丝醋,别的地方有的配醋,没有姜丝,那不行。蟹是寒性的,吃多了会肚子疼,姜丝能去寒,醋能提鲜,缺一不可。我年轻的时候,有个上海来的客人,吃汤包不蘸姜丝醋,结果吃了两笼就肚子疼,后来我给了他点姜丝,他嚼着吃了,才好点。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改。”
陆帆把老奶奶的话记在笔记本上,又问周老板:“周叔,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笼汤包啊?”
“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三百多笼,”周老板笑着说,“从早上六点开到晚上八点,忙的时候,我和王师傅、刘师傅都顾不上吃饭,中午就随便吃点包子垫垫。有时候客人多,要排队,有的客人从上海、南京过来,坐高铁来,就为了吃一笼我们家的汤包,说比他们那边的好吃。上次有个上海的客人,一次买了十笼,说要带回去给家人尝尝,我给他用保温箱装的,里面放了冰袋,能保六个小时,他回去加热了,说味道和刚蒸出来的差不多。”
他指了指门口的一个保温箱,保温箱是银色的,上面印着“老季家汤包”的字样:“那是给外地客人打包用的,我们用两层真空袋包装汤包,外面套保温袋,里面放的冰袋是自制的,用矿泉水瓶装的冰水,裹着毛巾,避免冻伤汤包。还要给客人一张加热说明,告诉他们怎么加热才不会让汤包破,怎么吃才好吃。”
陆帆吃完最后一个汤包,感觉胃里暖暖的,一点都不腻。周老板又给了他一碗大麦粥:“再喝点粥,垫垫肚子,等下逛老街的时候不容易饿。老街里还有很多好吃的,除了刚才你看到的老汁鸡和脆饼,还有卖豆腐脑的,是咸口的,加了虾米、紫菜、榨菜丁、香油,很好吃;还有卖麦芽糖的,是手工做的,甜而不腻;你还可以去江边的江堤上逛逛,那里能看到长江,风景好。”
喝完粥,陆帆付了钱,周老板还给他装了一小袋蟹黄汤包的馅料样品——是用小密封袋装好的,里面有蟹黄、蟹肉和肉馅,袋子上贴着一张小纸条,写着“老季家蟹黄馅,2023年10月25日”。“带回去给朋友看看,知道我们的馅料是真材实料,没有掺面粉,”周老板笑着说,“很多客人都怀疑我们的馅料掺了面粉,其实没有,我们做汤包做的是口碑,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陆帆接过袋子,心里很感动。他拿出手机,给周老板拍了张照片,照片里周老板站在汤包店的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竹编蒸笼,脸上带着憨厚的笑,身后的招牌上“老季家汤包店”几个字很醒目。“周叔,我把这张照片发在视频里,让更多人知道您家的汤包!”他说。
“好啊!”周老板笑着说,“谢谢你啊小伙子,要是张阿姨问起,你就说我问她好,让她有空来吃汤包,我给她留最新鲜的蟹!”
离开老季家,陆帆沿着老街慢慢逛。他先去吃了刚才老板推荐的豆腐脑,豆腐脑是用石膏点的,嫩得像布丁,勺子舀下去会颤,加了虾米、紫菜、榨菜丁、香油,还有一点辣椒油,鲜得很,一点都不腥。卖豆腐脑的阿姨说,她做豆腐脑做了二十年,用的是本地的黄豆,泡十二个小时,磨浆用石磨,比机器磨的香,“机器磨的黄豆太细,没了豆香味,石磨磨的才有小时候的味道。”
然后他又去买了一块季市脆饼,这次买的是核桃味的,核桃碎很多,咬起来很香。路过卖麦芽糖的老人身边时,老人笑着问他:“小伙子,要不要尝尝麦芽糖?我这麦芽糖是用麦芽和糯米做的,没有添加剂,甜而不腻!”陆帆买了一小块,放在嘴里嚼,甜丝丝的,还带着点麦芽的清香,很好吃。
走到老街的尽头,是一条江堤。江堤是用石头砌的,很高,上面铺着水泥路面,有不少人在散步。一位退休的老人在打太极,背景音乐是收音机里的锡剧《珍珠塔》,声音不大,却很有韵味。几个小孩在放风筝,风筝是沙燕形状的,飞得很高,线在手里绕着,家长在旁边喊“小心线割手”,声音里满是担心。
陆帆走到江堤边,靠在栏杆上,看着远处的长江。长江的水泛着波光,货轮慢慢驶过,汽笛声偶尔传来,带着点悠远的感觉。江风拂在脸上,带着蟹油的香和水汽的凉,很舒服。他拿出手机,给小苏发了条消息,拍了长江的照片和老季家的汤包照片,说:“老季家的汤包太好吃了!周叔还问你外婆好,让她有空来吃!”不一会儿,小苏回复:“太好了!我外婆肯定很高兴!对了,记得尝尝季市的老汁鸡,我外婆说比扬州的盐水鸭香!”
陆帆笑着回复“好”,然后拿出笔记本,继续写关于靖江蟹黄汤包的笔记:“靖江靠长江入海口,江鲜丰富,蟹黄汤包的灵魂在于‘鲜’——新鲜的长江中华绒螯蟹(三两以上雌蟹,当天拆,当天用)、新鲜的猪皮冻(熬煮三小时,无添加剂)、新鲜的鲜肉(本地猪的前腿肉,肥瘦比例3:7),缺一不可。手工擀皮的韧劲(0。5毫米厚度,高筋面粉+猪油)、十八道褶的讲究(锁住汤汁,美观)、姜丝醋的搭配(去寒提鲜,老祖宗的智慧),都是靖江人对美食的敬畏。周老板的坚守(继承父业,不忘初心)、老奶奶的回忆(与老伴的温情)、年轻情侣的甜蜜,让这笼汤包不仅有鲜味,还有人情味。这才是靖江蟹黄汤包最动人的地方——不仅好吃,还有故事。”
他打开手机,把刚才拍的汤包制作视频、周老板的照片、长江的照片发了出去,配文:“靖江季市老街老季家蟹黄汤包,一口入魂的江鲜!手工擀皮(0。5毫米),十八道褶,用的是长江新鲜雌蟹,汤鲜蟹香,配姜丝醋绝了!地址:靖江季市老街第三路口,记得提张桂兰阿姨,周老板会给你留最新鲜的蟹!”
不一会儿,评论就多了起来:“看起来好香!我下个月去靖江,一定去吃!”“博主太会找了,上次我去靖江吃的汤包一点都不好吃,这次跟着你去!”“请问可以快递吗?想吃!”“周老板看起来好憨厚,这样的店才靠谱!”陆帆笑着回复:“快递的话可以问周老板,他有保温箱包装,能保六个小时!”
收拾行李准备去常州时,陆帆特意在老季家买了两笼真空包装的蟹黄汤包——一笼给杭州的陈阿姨,一笼给自己。周老板很仔细地包装,用两层真空袋,外面套着保温袋,里面放了两个冰袋,还给他一张加热说明:“水开后蒸五分钟,不能蒸太久,不然皮会破;吃的时候记得‘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别烫到嘴。”他还送了陆帆一小瓶自制的姜丝醋,说:“回去加热汤包,蘸这个醋才够味,外面买的醋没这么香。”
陆帆付钱时,周老板多找了五块钱,说:“第一次来,算个见面礼,下次再来,我给你打九折!”陆帆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心里暖暖的。
坐在前往常州的客车上,陆帆靠在车窗上,手里拿着那袋蟹黄汤包,心里想着刚才吃汤包的场景——周老板的憨厚笑容、王师傅娴熟的擀皮动作、刘师傅灵活的捏褶子手指、老奶奶温柔的回忆、年轻情侣的甜蜜,还有长江的壮阔、老街的热闹、蟹油的香气,这些都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回放。
他知道,接下来还有常州的银丝面、无锡的酱排骨等着他去探索,但靖江的这笼蟹黄汤包,会像扬州的大煮干丝一样,成为他旅程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因为它不仅有鲜美的味道,还有背后那些温暖的人和故事。这些人和故事,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有温度的,它们会成为他书稿里最动人的素材,让他的书不仅有美食的介绍,还有人情的温暖。
客车路过常州界碑时,陆帆看到“常州欢迎您”的红色大字,旁边画着一碗银丝面,面条细得像头发丝。他想起小苏说的“常州银丝面细得像头发丝,煮在汤里不会断,鲜得很”,心里充满了期待。他拿出笔记本,在“靖江蟹黄汤包”那页的后面,写下“常州银丝面”五个字,旁边画了一碗细面条,然后笑着闭上眼睛,开始想象银丝面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