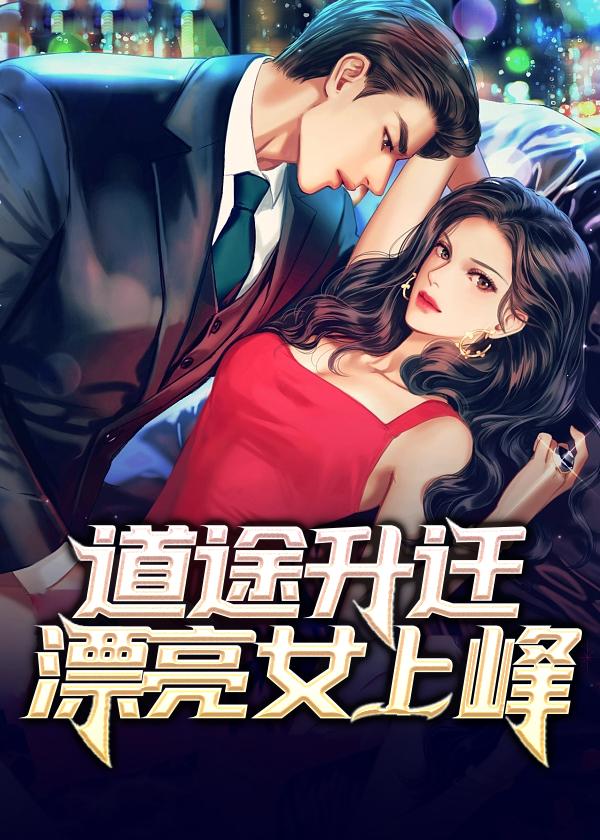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我的足迹在哪里查找 > 第67章 淮安软兜长鱼运河之都的鳝鱼艺术(第2页)
第67章 淮安软兜长鱼运河之都的鳝鱼艺术(第2页)
“关键在新鲜和火候”,李师傅喝了口茶,“鳝鱼要现杀现做,不能放;炒的时候火要控制好,既要炒出香味,又不能炒老。我父亲以前说,做软兜长鱼,就像跟鳝鱼‘对话’,你得懂它的脾气,才能做出它的鲜。”
邻桌的一位老人听到他们的对话,笑着插了句嘴:“小伙子,你是第一次来淮安吃软兜长鱼吧?李师傅的手艺在淮安可是数一数二的,我年轻时在漕运码头当会计,每次有重要客人,都来这儿点软兜长鱼。”老人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花白,手里拿着一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淮安漕运局”的蓝色字样,杯口有些磨损,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
陆帆点点头,好奇地问:“大爷,以前漕运码头的人都爱吃软兜长鱼吗?”
老人放下杯子,叹了口气,眼里满是回忆:“那时候啊,船工们跑运河,从淮安到苏州,要走三西天,体力消耗大,就爱吃点荤的。鳝鱼在运河里多,容易捕,还便宜,又能补身体,所以软兜长鱼就成了码头的‘硬菜’。那时候李师傅的父亲在码头上开了个小摊子,每天都有很多船工来吃,有时候要排队到天黑。”
“那时候的软兜长鱼,做法比现在简单”,老人继续说,“就是用猪油炒,加一点黄酒和盐,没有现在这么多调料,却一样鲜。船工们坐在摊子前,一碗软兜长鱼,一碗米饭,吃得满头大汗,都说‘解乏’。”他指着窗外的里运河,“你看,那时候运河上的商船往来不断,船上都带着蒲兜,里面装着鳝鱼,到了码头就找李师傅的父亲做软兜长鱼。”
李师傅补充道:“以前淮安是运河之都,南北商船都在这儿停靠,带来了各地的食材和口味,软兜长鱼就是在那时候发展起来的——既有南方菜的细腻,又有北方菜的厚重,很合船工们的口味。后来漕运慢慢衰落了,但软兜长鱼却留了下来,成了淮安的招牌菜。”他给陆帆的盘子里又添了一块鳝鱼,“再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陆帆拿起筷子,夹起面条,倒进软兜长鱼的酱汁里。面条是手擀的阳春面,煮得软硬适中,吸满了浓稠的酱汁后,变得格外入味——面条的软、酱汁的鲜、鳝鱼的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吃一口,满足得让人想叹气。他又喝了一口酱汁,酱汁浓稠得能挂在勺子上,鲜得能掉眉毛,没有一点多余的调料味,只有鳝鱼本身的鲜和猪油的香。
“姜丝别忘了吃”,李师傅提醒道,“姜丝是用醋泡过的,能解腻,还能去鳝鱼的腥味。”陆帆夹了一点姜丝,放进嘴里,醋的酸、姜的辣,瞬间中和了猪油的油腻,让口腔里清爽了不少,也让接下来的每一口都更有滋味。
吃完软兜长鱼,陆帆的碗底只剩下一点酱汁。李师傅看着他,笑着说:“要不要再加点汤?很多人都喜欢用汤泡饭。”陆帆点点头,李师傅转身去后厨,很快端来一小碗热汤——是用鳝鱼骨熬的,奶白色的汤里飘着一点葱花,喝一口,鲜得让人眼睛一亮。“这汤是用鳝鱼骨熬的,熬了一个小时,没加任何调料,就加了一点姜片”,李师傅说,“以前船工们都爱喝这个汤,说能补身体。”
陆帆把汤倒进米饭里,米粒吸满了汤的鲜,吃一口,比任何佐餐小菜都要香。他边吃边看窗外,里运河上的游船慢慢驶过,船上的游客举着相机拍照,阳光洒在水面上,泛着金色的光,像撒了一层碎金子。
结完账,李师傅从柜台后拿出一个纸袋子,递给陆帆:“这是淮安的特产茶馓,用麻油做的,脆得很,你带回去尝尝。”陆帆接过袋子,能闻到里面传来的麻油香,“谢谢李师傅,今天的软兜长鱼太好吃了。”
“下次来淮安,还来我这儿”,李师傅笑着说,“我给你做不一样的软兜长鱼,比如用蒜苔炒的,或者用洋葱炒的,都好吃。”
走出餐馆,里运河的风迎面吹来,带着淡淡的水汽和花香。陆帆沿着河边的步道走,岸边的石栏杆上刻着漕运的图案——有商船、船工、码头,还有人们吃软兜长鱼的场景,每一幅都生动得像活的一样。偶尔有路人经过,看到他手里的纸袋子,笑着说:“这是老淮猪的茶馓吧?他家的软兜长鱼最好吃了。”
走到漕运总督署遗址时,陆帆停下了脚步。遗址的大门是朱红色的,门楣上挂着“漕运总督署”的黑色匾额,匾额上的字苍劲有力,透着几分威严。门口的石狮子威武雄壮,身上的花纹还清晰可见,虽然历经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姿态。
走进遗址,里面陈列着很多漕运时期的文物——有船工穿的粗布衣服、用了几十年的船桨、记载漕运路线的账本,还有一个用蒲草做的兜子,跟李师傅店里的一模一样。“这个蒲兜是清朝时期的,用来装鳝鱼的”,讲解员指着蒲兜介绍道,“那时候运河上的船工捕了鳝鱼,就用这种蒲兜装着,蒲兜透气,能保持鳝鱼的新鲜,而且轻便,方便携带。”
陆帆看着蒲兜,想起李师傅说的“软兜”名字的由来,心里忽然觉得格外亲切——原来这道美味,己经在运河边流传了几百年,从清朝的漕运船工,到现在的游客,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品味着这份来自运河的鲜。
从漕运总督署出来,陆帆又去了镇淮楼。镇淮楼矗立在淮安老城区的中心,青砖灰瓦,飞檐翘角,楼顶上的琉璃瓦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登上楼顶,能看到整个淮安老城区的景色——里运河像一条碧绿的绸带绕着老城,岸边的柳树、青砖房、红灯笼,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楼里陈列着淮安菜的历史,其中就有软兜长鱼的介绍,文字旁边配着一幅画:画的是李师傅的父亲在漕运码头做菜的场景,旁边围了几个船工,笑得一脸灿烂。画下面写着一行字:“淮安软兜长鱼,始于明清,漕运文化的美食结晶,以鲜、嫩、香著称,是淮扬菜的代表之一。”
陆帆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写道:“淮安,运河之都。软兜长鱼不是一道简单的菜,是里运河的水养出来的鲜,是漕运船工的汗浸出来的香,是一代又一代人传下来的手艺。选笔杆粗的活鳝鱼,现杀去骨,用猪油爆炒,加本地黄酒、自制酱油、现磨胡椒,焖两分钟,简单的做法里藏着大大的智慧。吃的不仅是鲜,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情怀,是运河人家对生活的热爱。”
傍晚时分,陆帆来到里运河文化长廊。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河面上,像铺了一层金箔。岸边的红灯笼亮了起来,像一串串红色的星星,倒映在水里,形成一片璀璨的光影。有市民在河边散步,有的牵着狗,狗尾巴摇得欢快;有的推着婴儿车,婴儿车里的孩子笑着拍手;还有的在跳广场舞,音乐声、笑声、河水声混在一起,格外热闹。
陆帆坐在河边的石凳上,拿出手机,开启了首播。镜头对着里运河的夜景,他笑着说:“大家好,我现在在淮安的里运河边,刚吃了正宗的软兜长鱼,鲜得我现在还在回味。淮安是运河之都,这里的每一道菜都带着运河的味道——软兜长鱼用的是里运河的鳝鱼,熬汤用的是里运河的水,连酱油都是用运河边的黄豆酿的。”
首播间里的粉丝很快活跃起来:
“看起来好好吃!求餐馆地址!”
“软兜长鱼是什么?第一次听,听起来好有意思。”
“主播,鳝鱼会不会很腥啊?我一首不敢吃。”
“求做法!想在家试试!”
陆帆一一回复,还把白天跟李师傅学的“三选三不选”和制作步骤分享给大家:“选笔杆粗的活鳝鱼,背部发黑的,现杀现做;用猪油爆炒,加本地黄酒和酱油,现磨胡椒,焖两分钟就好,一点都不腥,大家可以试试。”他还拿起李师傅给的茶馓,对着镜头晃了晃,“这是淮安的茶馓,用麻油做的,脆得很,配软兜长鱼的汤刚好。”
首播快结束时,一个粉丝留言:“主播,我爷爷以前是漕运船工,他说以前在码头吃过软兜长鱼,说特别鲜,可惜现在爷爷不在了,我一首想尝尝。”陆帆看着这条留言,心里忽然有点酸,他回复道:“如果你来淮安,一定要去‘老淮猪’餐馆尝尝,李师傅的软兜长鱼,还是以前的味道,能让你想起爷爷说的鲜。”
首播结束后,陆帆站起身,准备离开淮安,前往下一站宿迁。他走到车站,手里拿着李师傅给的茶馓,嘴里还留着软兜长鱼的鲜味儿。想起白天的经历——李师傅的笑容、老人的故事、漕运总督署的文物、里运河的夜景,心里满是满足。他忽然明白,旅行的意义不仅是品尝美食,更是感受美食背后的文化,认识那些可爱的人,听那些带着温度的故事。
大巴车驶出淮安时,陆帆回头看了一眼里运河。夜色中的河水泛着淡淡的光,像一条流动的银河,岸边的红灯笼渐渐变小,最后变成一个个小小的光点。他掏出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道:“淮安,再见。谢谢你的软兜长鱼,谢谢你的里运河,谢谢你的故事。下次我还会来,再来吃李师傅的软兜长鱼,再来听漕运的故事。下一站,宿迁,乾隆贡酥,我来了。”
大巴车在夜色中行驶,陆帆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嘴角忍不住上扬——里运河的风、软兜长鱼的鲜、李师傅的笑声,像一幅温暖的画,留在了他的记忆里,也留在了他的书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