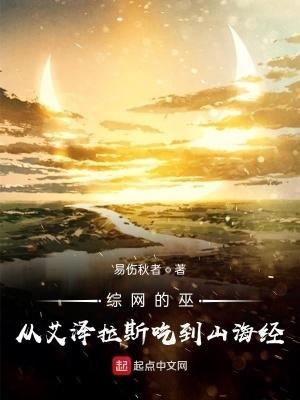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续写大明风华 > 第99章 监国风雨 大军凯旋(第1页)
第99章 监国风雨 大军凯旋(第1页)
朱棣的銮驾消失在德胜门外的尘烟中时,朱高炽正站在文华殿的丹陛上,望着那面渐行渐远的玄色纛旗。春风卷起他宽大的常服袖口,露出腕间那串徐妙云亲手穿的蜜蜡佛珠,每颗珠子都被得温润发亮。身后的太监捧着监国玉玺,沉甸甸的玉质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像块压在心头的石头。
文华殿的案头就堆起了如山的奏折。朱高炽望着那些贴着“加急”标签的卷宗,指节因用力按压太阳穴而泛白。昨夜批改北征粮草账册到三更,喉头的痒意此刻化作剧烈咳嗽,帕子上又添了几点刺目的猩红。
“太子殿下,山东巡抚八百里加急,说黄河决堤了。”太监捧着奏折的手簌簌发抖,蜡封上的“汛”字被水洇得模糊。朱高炽猛地站起,玄色常服的下摆扫过案头,带倒的砚台在《河工图》上泼出大片墨渍。图中用朱砂标注的堤坝薄弱处,正巧是黄河九曲最险的“铜瓦厢”。
他踉跄着扑到舆图前,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面。山东布政使是李景隆的门生,上月才以“国库空虚”为由,驳回了加固堤坝的奏请。如今洪水滔天,淹没的何止是良田,更是他监国的威信。“传旨,命夏原吉即刻赶往山东,带足经纬缎防水布和粮草。”朱高炽的声音因咳嗽变得沙哑,“告诉夏尚书,不惜一切代价堵决口,灾民安置用经纬缎帐篷,绝不能出乱子。”
可旨意刚拟好,吏部尚书就捧着弹劾奏折闯进殿:“太子殿下,夏原吉乃建文旧臣,此刻委以重任,恐生变数!”老臣花白的胡须颤抖着,“况且动用三万匹经纬缎赈灾,太过奢侈,御史台己联名上书……”
朱高炽攥着奏折的手指青筋暴起,忽然将卷宗狠狠砸在地上:“奢侈?等灾民反了,你用什么去堵!”他胸口剧烈起伏,望着殿外阴沉的天空,想起父皇临走前的叮嘱“监国当刚柔并济”,可面对这群只知党争的老臣,柔肠寸断也换不来半分体谅。
更棘手的事接踵而至。北平传来急报,朱高燧以“防备蒙古偷袭”为由,私自调动了一万京营兵力。奏报上的字迹张扬,竟在末尾添了句“兄长体弱,恐难兼顾北疆”。张小小捧着密信进来时,正撞见朱高炽将茶杯重重掼在地上,青瓷碎片混着茶水溅湿了龙纹地毯。
“他这是明目张胆地夺权!”朱高炽的咳嗽声震得案头烛台摇晃,“父皇刚走半月,他就敢如此放肆!”张小小捡起碎片,见他指缝渗出血珠,忙取出伤药:“眼下北征在即,不能自乱阵脚。”她指着密信上的调兵路线,“你看,他的兵力都集中在北平城外,像是在防备什么,或许……”
话音未落,锦衣卫指挥使匆匆求见,呈上的密报让朱高炽如坠冰窟。李景隆与朱高燧的亲信在酒馆密会,席间竟提及“若太子有恙,赵王可暂代监国”。泛黄的纸页上,还沾着酒渍与油渍,仿佛能闻到那股阴谋的酸腐味。
“传我令,让朱瞻基去北平慰问将士。”朱高炽忽然冷静下来,用布巾裹住流血的手指,“告诉赵王,皇长孙代天巡狩,让他好生接待。”张小小眼中闪过亮光——让朱瞻基这个“好圣孙”去北平,既给了朱高燧警告,又不失皇家体面。
可朝堂的风浪远未平息。江南士族借着黄河水灾发难,弹劾夏原吉“滥用救灾物资”,连带着经纬缎也成了“祸国之物”。御史台的奏折堆在御案上,字字句句都在指责太子“识人不明”。朱高炽在文华殿与群臣争执到日暮,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最后拍着龙椅扶手嘶吼:“你们谁敢说,用经纬缎帐篷让灾民免于冻毙,是错的!”
退朝时,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瘦长。朱高炽扶着丹陛的栏杆喘息,望着空荡荡的奉天殿,忽然觉得这监国的位置比北征的战场更凶险。父皇的龙椅看着威严,坐上去才知如坐针毡,每一道圣旨都像在薄冰上行走,稍不留意就会坠入深渊。
深夜的东宫,张小小给朱高炽熬了润肺汤,见他对着山东灾情图出神。图上用红笔圈出的“受灾县”密密麻麻,像片刺眼的血渍。“夏尚书传来消息,决口己堵住一半,就是缺人手。”她轻声道,“要不,从京营调些兵过去?”
朱高炽摇头,咳得更厉害了:“京营不能动,朱高燧在北平虎视眈眈。”他拿起朱瞻基从北平寄来的家书,见上面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写着“舅舅待我很好,还带我看了军甲”,眉头才舒展些许。“这孩子,倒会缓和气氛。”
可没等他喘口气,边关又传来急报——阿鲁台的侄子率小股骑兵偷袭了宣府,抢走了一批北征的粮草。朱高炽连夜召集兵部议事,将军们吵成一团,有的说要派兵追击,有的说要固守待援。他看着舆图上宣府到北平的距离,忽然想起父皇教他的“以静制动”,却在众将的争执中,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无力。
窗外的梧桐叶被夜雨打得噼啪作响,朱高炽对着烛火咳嗽不止。张小小给他披上披风,见他鬓角又添了几缕白发。“要不,给父皇写封信?”她试探着问。朱高炽摇头,将咳出的血帕子藏进袖中:“父皇在前方打仗,不能让他分心。”他望着案头堆积的奏折,忽然苦笑,“原来监国,比打仗还难。”
这夜,东宫的烛火亮到天明。朱高炽在奏折上批下“准夏原吉调山东民夫助修堤坝”“令宣府守将加强戒备,勿要追击”,每一个字都写得异常艰难。他知道,这只是监国风雨的开始,往后的路,只会更难走。而他能做的,唯有咬牙撑着,不让父皇在北征路上,还要为后方担忧。
当早朝的钟鼓声在奉天殿响起时,张小小正站在织房的高台上,看着工匠们将银灰色的经纬缎裁成箭囊。这种混纺了西域羊毛的布料,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不仅轻便,还能防箭矢穿透。“再加快些!”她对管事的老织工说,“陛下的大军己经过了居庸关,这些箭囊要在五月前送到宣府。”
五月的风带着暖意吹进东宫时,朱瞻基从太学院回来,手里捧着先生批改的《北征策》。他跑到织房,见母亲正在教朱瞻墉辨认棉花,便献宝似的递上文章:“母亲你看,先生夸我写的‘经纬缎帐篷防火法’好呢!”张小小接过文章,见上面画着简单的防火示意图,用朱砂笔圈出的“涂桐油”三个字旁,还有先生批注的“可行”。
“倒是个好主意。”她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明日让织工试试,若是可行,就给北征的将士们都换上。”朱瞻基用力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母亲,方才路过兵部,听见父亲和夏尚书说,阿鲁台退到克鲁伦河以北了,父皇打算乘胜追击。”他学着大人的模样皱起眉头,“先生说漠北的夏天蚊虫多,将士们的帐篷够吗?”
张小小望着远处宫墙上飘动的“东宫监造”旗帜,轻声道:“够的,我们准备了三倍的帐篷,还有能防蚊虫的硫磺经纬缎。”她拉起儿子的手,“走,去看看你父亲,他今日处理奏折到现在还没歇呢。”
暖阁里,朱高炽正对着舆图出神,案头的润肺汤己经凉了。见张小小进来,他指着地图上的“胪朐河”:“高煦的先锋营己经到了这里,父皇的大军明日就能会师。”他咳嗽几声,拿起凉了的润肺汤就要喝,被张小小拦住:“我去让御膳房热一下。”
朱高炽拉住她的手:“不用了,还有几份奏折要批。”他看着妻子鬓边的银簪,忽然笑道,“这些日子辛苦你了,经纬缎的事办得很好,父皇在军报里都夸了。”张小小坐在他身边,看着他苍白的脸,轻声道:“都是为了大明,为了将士们能平安回来。”
六月的骄阳炙烤着京城,织房的工匠们却忙得满头大汗。新到的一批经纬缎被染成了军绿色,这种用艾草汁染的颜色,在草原上不容易被发现。张小小站在染坊前,看着布匹在染缸里翻滚,忽然觉得这深宫里的日子,就像这染布,看似单调,实则藏着万千变化。
这日,朱高炽从朝堂回来,脸色格外凝重。张小小见他眉头紧锁,连忙递上一杯凉茶:“出什么事了?”朱高炽接过茶杯,一饮而尽:“刚接到军报,阿鲁台假意投降,却在克鲁伦河设了埋伏,父皇的大军中了计,损失了些兵马。”他重重地叹了口气,“高煦己经率军去支援了,但愿能没事。”
张小小的心猛地一沉,指尖攥紧了手中的经纬缎:“那粮草和甲胄还够吗?要不要再送些过去?”朱高炽点头:“我己经让夏原吉准备了,明日就出发。”他看着妻子担忧的眼神,握住她的手,“别担心,父皇和高煦都是身经百战的,会没事的。”
夜色渐深,东宫的烛火还亮着。张小小坐在灯下,给北征的将士们绣平安符,经纬缎上的“平安”二字,绣得格外用力。她想起朱棣出征前的模样,想起朱高煦的勇猛,想起那些穿着经纬缎甲胄的将士们,心中默默祈祷着他们能平安归来。
七月的风带着秋意,吹黄了御花园的梧桐叶。朱高炽在文华殿收到了捷报,朱棣和朱高煦合力击溃了阿鲁台的埋伏,正在乘胜追击。他拿着捷报的手微微颤抖,连忙让人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张小小。
张小小在织房听到消息时,正和林氏讨论新的织布技法。她放下手中的布料,眼中泛起泪光:“太好了!将士们终于可以少受些苦了。”林氏也笑着拍手:“等他们凯旋,我们用最好的经纬缎给他们做新衣裳!”
秋意渐浓,北征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朱棣的大军己经深入漠北,阿鲁台的残部望风而逃。朱高炽在京城主持秋闱,选拔了不少有才能的进士,其中有几个还精通织布技法,被他派到江南织造,协助推广经纬缎。
张小小看着织房里堆积如山的经纬缎,忽然觉得这布料不仅能做甲胄和帐篷,还能做百姓穿的衣裳。她让苏氏编了本《经纬缎民用辑要》,详细介绍了布料的织法和用途,打算在全国推广。“若是百姓们都能穿上这种舒服的布料,也算没白辛苦一场。”她对赵氏说,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九月初九这日,重阳节的茱萸香弥漫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朱高炽在午门迎接了北征的先头部队,为首的正是朱高煦。他身披铠甲,脸上带着风霜,见到朱高炽时,难得露出了笑容:“大哥,我们打赢了!”朱高炽走上前,兄弟俩紧紧相拥,多年的隔阂仿佛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张小小站在东宫的角楼上,望着远处凯旋的大军,心中充满了欣慰。她知道,这场北征的胜利,不仅是将士们的功劳,也是无数人在后方默默付出的结果。而那些经纬交织的布料,就像一条条无形的线,将所有人的心都连在了一起,共同编织着大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