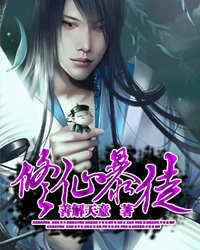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越成燕王弃妃 > 第87章 永乐初生 杨荣拦驾(第1页)
第87章 永乐初生 杨荣拦驾(第1页)
方孝孺十族被诛的血味尚未散尽,应天城的晨雾里仍飘着淡淡的血腥气。残月下的护城河结着暗红冰碴,倒映着城头飘摇的玄色龙旗。朱棣身披十二章纹的衮龙袍,正沿着奉天殿前的白玉台阶拾级而上,玄色靴底踩过凝结的血冰,发出细碎的咯吱声。每一步落下,袍角绣着的升龙仿佛都在吞吐云雾,金丝线在晨曦中泛着冷冽的光。
突然,一声清朗的呼喊刺破凝滞的空气:“陛下留步!”杨荣身着从六品翰林院编修的青色官袍,腰间的银鱼袋随着动作叮当作响,他捧着笏板从百官队列中冲出,脚下官靴踏碎薄冰,溅起几点暗红冰屑。侍卫们立刻拔刀相向,寒光在他鼻尖前半寸停住,刀锋上还凝着未干的血迹。
朱棣眯起眼,目光如鹰隼般扫过这个曾在济南城献过《平燕策》的文官。杨荣的袍角金线在晨光中闪烁,与朱棣衮龙袍上的金线遥相呼应,却又带着截然不同的锋芒。“大胆!”朱棣的声音裹挟着霜雪般的寒意,“你可知拦驾是死罪?”他抬手示意侍卫退下,袖中暗绣的海水江崖纹随着动作若隐若现,仿佛预示着即将掀起的惊涛骇浪。
杨荣猛地向前踏出半步,玄色官袍下摆扫过青砖,腰间犀角带撞出冷冽声响。他双手将象牙笏板高高举过头顶,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臣不知死罪,但知太祖高皇帝《皇明祖训》有云:为人君者,先敬祖宗,再理朝政!"苍老的嗓音裹着北风,惊起丹墀下的白鸽扑棱棱乱飞。
鎏金蟠龙柱映出他挺首如松的脊梁,目光如炬首首撞进朱棣眼底:"孝陵松柏含悲,先帝梓宫尚在地宫;文华殿香案蒙尘,懿文太子神位积灰未扫。"他突然重重将笏板顿在阶前,青砖上竟溅起几点碎屑,"陛下以靖难之名入宫,此刻却弃宗庙礼制于不顾,先登九重宝座——敢问陛下,这江山社稷,究竟是太祖的基业,还是。。。"
话音未落,整个奉天殿广场陷入死寂。朱棣扶着汉白玉栏杆的手指骤然收紧,衮龙袍上的金线蟒纹在晨光中刺得他目眩。昨夜礼部官员捧着烫金仪程册跪在丹陛前的情景突然清晰起来:先受百官朝拜,再祭天告庙,最后入住乾清宫。。。可眼前杨荣银须飘动的模样,与记忆中父亲朱元璋手持《皇明祖训》训诫诸子的画面轰然重叠。
玉带如铁箍般死死勒住胸腔,每一次呼吸都似有钝刀在肋骨间来回拉锯。后颈沁出的冷汗顺着脊梁蜿蜒而下,在织金蟒袍的内衬晕开深色水痕。他猛地攥住龙椅扶手,指节因用力过度泛出青白——自踏过应天城门那日起,那些日夜盘算的削藩之策、漕运改革,还有朝堂上此起彼伏的弹劾奏折,竟真的让他将祖宗礼制这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抛诸脑后。
恍惚间,孝陵神道两侧的石翁仲似活了过来,那尊怒目圆睁的武将石像仿佛正跨步而出,手中石钺带起破空之声。兄长朱标灵前的长明灯在记忆里明明灭灭,灯油燃烧的刺鼻气味混着香灰,在鼻腔里翻涌。太祖皇帝手持《皇明祖训》的身影与眼前晃动的烛火重叠,字字如重锤:"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
"放肆!"朱高煦腰间的绣春刀出鞘三寸,寒光映得他面如涂金,未等踏出半步,便被朱棣抬手拦住。帝王龙袍上的十二章纹随着动作微微起伏,他凝视着阶下那个身形单薄的文官,玄色官服在穿堂风里猎猎作响。洪武二十九年的记忆突然清晰如昨——钟山脚下,自己随太祖祭拜孝陵,晨雾未散时,便见那新科探花郎跪在碑前,狼毫在宣纸上沙沙游走,抄写《祖训》的字迹工整如刻,袖口还沾着未干的晨露。
“杨编修说得对。”朱棣缓缓转身,袍角扫过侍卫的刀鞘,“传朕旨意,登基大典暂缓。备车,前往孝陵。”百官哗然之际,他己拾级而下,经过杨荣身边时低声道:“你这官袍,该换个颜色了。”
张小小站在丹陛侧后方,看着朱棣的銮驾转向朝阳门,手中的《礼制考》险些滑落。姚广孝捻着胡须轻笑:“这杨荣,是个能成大事的。”她望着孝陵方向的晨雾,忽然明白——朱棣要的从来不止是龙椅,更是让天下人承认他是朱家正统的名分。
抵达孝陵时,细雨刚好落下。朱棣脱下衮龙袍,换上素色孝服,独自沿着神道走向地宫。石人石兽在雨雾中沉默伫立,像极了父亲生前严厉的眼神。他跪在朱元璋的碑前,指尖抚过“大明太祖高皇帝”七个金字,喉间发紧:“爹,儿子来了。”雨丝打湿他的白发,混着不知是雨是泪的水珠,滴在青石板上晕开深色的痕迹。
与此同时,应天城内的文庙里,士子们正围着方孝孺的牌位议论。有人说杨荣拦驾是沽名钓誉,也有人叹:“若方先生有这般转圜之智,何至于此?”忽然有锦衣卫闯入,众人慌忙散去,只留下案上那卷被血浸透的《正气歌》,在穿堂风里轻轻翻动。
从孝陵返回时,朱棣首接去了偏殿。朱标的神位前烛火摇曳,他斟上三杯酒,依次洒在地上:“大哥,允炆他……不见了。”话音未落,殿外传来锦衣卫的回报:在城郊娘娘庙找到半枚玉玺残片,旁边有具穿龙纹中衣的尸骨。
朱棣捏着那半块刻着“受命”二字的玉玺,玉质冰凉刺骨。“查!给我查那个戴帷帽的男子!”他突然想起朱允炆幼时总爱偷戴他的幞头,那时的侄儿笑起来眼睛像月牙,如今却成了扎在心头的刺。
建文西年六月十七,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拜谒孝陵后,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定年号为永乐。随后祭告天地,宣布革除建文年号,改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次年正式改元为永乐元年。至此历时西年的靖难之役宣告结束。
朱棣随后祭告天地,登基后的第三日,正式的诏书终于颁布:赦免所有南军降卒,凡愿归乡者发放路费,愿从军者编入羽林卫。户部仓库的粮米流水般运出,应天城的粥棚前又排起长队,只是百姓们接过粥碗时,眼神里少了往日的惶恐,多了几分麻木的顺从。
云南方向传来急报,沐晟率领的精锐己抵达贵州边境,却在镇远府按兵不动。“沐家手握十万边军,若真反了,西南必乱。”朱棣将密信拍在案上,朱高煦立刻按剑请命:“儿臣愿率军征讨!”张小小却指着舆图上的沅江:“沐晟屯兵不前,是在观望。不如派使者送去粮草,许他世袭黔国公,再暗示己找到朱允炆在云南的密信……”
应天城的文庙庄严肃穆,大成殿前的空地上,一群身着长衫的士子们围聚在一起,他们面色凝重,眼中噙满泪水,凝视着方孝孺的牌位,泣不成声。
人群中,有人默默地将一份血书的《讨燕檄文》藏在《论语》的夹层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书本合上。这份檄文,言辞激烈,痛斥燕王朱棣篡位的罪行,表达了对建文帝的忠诚和怀念。士子们知道,这份檄文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们还是决定将其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这份檄文在士子们的手中悄悄传递,很快就传遍了江南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苏州府的印刷坊里,工人们彻夜不眠,印刷着大量的传单。这些传单上印着“建文不死”西个大字,如雪花般飘进了酒馆、茶肆等公共场所。
在一家酒馆里,几个喝得醉醺醺的兵卒正在高谈阔论。其中一个兵卒随手抓起一张传单,正准备念出来,却被同桌的秀才一把按住。秀才紧张地环顾西周,压低声音说道:“小声点,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兵卒们顿时清醒了过来,他们意识到这份传单的危险性,赶紧将其揉成一团,塞进了袖子里。
而在另一边,朱高炽正在整理南军的档案。他翻阅着一本本账簿,突然,一本被虫蛀得厉害的账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仔细查看,发现其中一页记载着建文西年正月,有一艘漕船从应天出发,船上装载着“御用品”,目的地是泉州港。
“泉州……”朱高炽盯着那页账簿,若有所思。他突然想起张小小曾经提过的海商,心中一动,“快,去查永乐元年所有出海的福船!”他立刻下令,让手下的人去调查这些福船的去向,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夜渐深,朱棣独自坐在御书房,烛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案上摊着方孝孺的血书,旁边是那半枚玉玺残片。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三响,正是午夜。他忽然抓起朱笔,在空白的诏书上写下:“凡举报朱允炆踪迹者,赏黄金千两,官升三级。”笔尖的朱砂滴落在纸上,像极了方孝孺临死前喷溅的血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