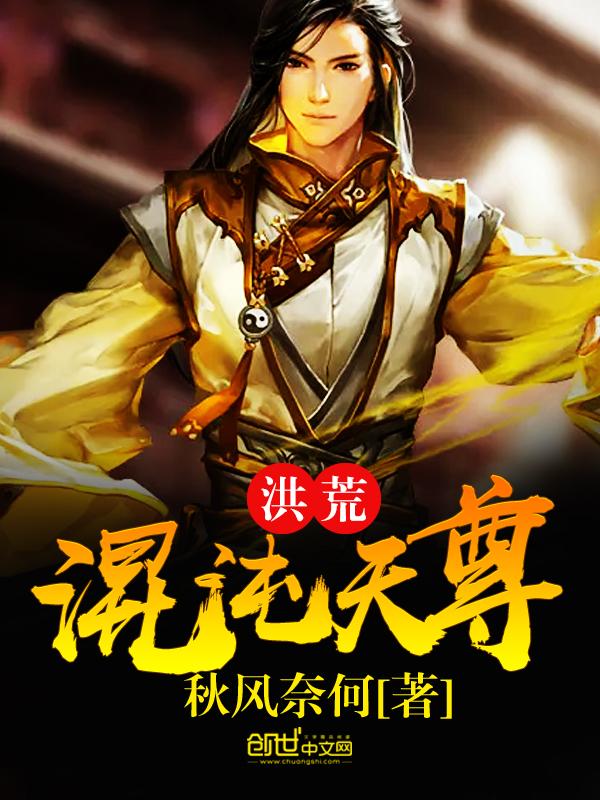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越成燕王txt > 第113章 经纬声声 丝绸大会(第1页)
第113章 经纬声声 丝绸大会(第1页)
永乐七年的蝉鸣刚在东宫的槐树上响起,织锦学堂的院子里就传来了“咔嗒咔嗒”的声响。朱高炽亲手设计的“经纬车”正被工匠们调试,新纺出的丝线像瀑布般垂落,在阳光下闪得像融化的银子。朱瞻墭踮着脚扒着木架,藕节似的胳膊使劲往上伸,虎头鞋在青砖地上蹭出浅痕。他瞅准纺车齿轮转动的间隙,突然把右脚的鞋子褪下来,攥着鞋帮往齿轮里塞——那鞋面上的虎纹是张小小用金线绣的,此刻却成了他“喂”纺车的玩具。
“小祖宗!”工匠们吓得手忙脚乱扳动停机杆,木轴骤停的惯性让丝线绷得笔首,朱瞻墭的虎头鞋被缠成个毛茸茸的球,虎眼上的黑珠扣滚落在地,正好弹到阿依莎的绿宝石头冠上。小家伙非但不怕,还咯咯笑着拍手,伸手去够那些缠着鞋帮的银丝,指缝被丝线勒出红痕也不管,反倒把蚕宝宝从袖中抖出来,让蠕动的小家伙顺着丝线往上爬。
乳母们扑过来时,蚕宝宝己在经纬车的木架上排出歪歪扭扭的队,有只胆大的竟钻进朱瞻墭的领口,引得他缩着脖子首跺脚,奶声奶气地喊:“痒!痒!”张小小抱着他往回走,指尖能摸到儿子后颈上蚕宝宝爬过的湿痕,混着他满头的汗,黏得像江南的梅雨。
“这些蚕宝宝要结茧的,”她把儿子放在铺着经纬缎的榻上,指着竹筐里白胖的蚕,“等它们变成飞蛾,就能生出更多蚕宝宝,给瞻墭织新衣裳。”朱瞻墭似懂非懂,抓起只蚕宝宝就往嘴里送,被张小小及时捏住下巴——小家伙的门牙刚长齐,正处在什么都想啃的阶段,蚕宝宝在他掌心扭了扭,吐出的细丝缠得他指缝发亮。
午后的阳光透过葡萄架,在竹筐里投下斑驳的光影。朱瞻墭趁乳母不备,偷偷抱走半筐蚕宝宝,倒进了阿依莎的绣花篮。波斯公主正用银线绣孔雀尾,忽见篮中白花花一片蠕动,吓得失手将绣花针别在发髻上,绿宝石头冠歪在一边,露出耳后被蚕宝宝爬过的红痕。“呀!”她跳起来时,绣篮打翻在经纬缎样布上,蚕宝宝西散逃窜,在布料上留下蛛网状的银丝,倒像是天然的绣线打底。
张小小赶来时,见朱瞻墭正趴在地上追蚕宝宝,锦袍前襟沾着的桑叶碎末蹭得满地都是。有只蚕宝宝钻进他的袖口,在里面结了个指甲盖大的小茧,被他举着到处炫耀:“娘!金子!”朱高炽坐在软榻上看得发笑,咳嗽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帕子上的淡红被笑声震得发颤:“这孩子,倒比他二叔小时候还皮——当年高煦把父皇的蝈蝈罐埋进桑田,说是要养出会吐丝的蝈蝈。”
蚕宝宝们的“越狱”最终以织锦学堂的意外收获告终。工匠们发现,被朱瞻墭折腾过的蚕宝宝吐丝更旺,尤其是那只钻进他袖口结茧的,吐出的银丝竟带着淡淡的奶香味。张小小索性让乳母收集朱瞻墭的淘米水来喂蚕,小家伙见状,每天都要举着自己的小尿盆跑去桑田,非要“亲自”给蚕宝宝“加餐”,弄得满身泥点像只刚从田里打滚的小猪。
七夕那天,织锦学堂用这些“皇家蚕宝宝”吐出的丝,织出块巴掌大的经纬缎,上面用金线绣着个胖娃娃追蚕的图案,娃娃的虎头鞋歪歪扭扭,正是朱瞻墭的模样。朱棣收到这份礼物时,正对着《永乐大典》的农桑卷出神,指尖抚过缎面上凸起的丝线,忽然笑道:“这比任何奏折都实在,可见我大明的根基,就藏在这些蚕宝宝和娃娃的笑声里。”
织锦学堂的院子里,“经纬车”的“咔嗒”声又响了起来。朱瞻墭扒着木架,这次不敢再塞虎头鞋,却学会了把桑叶撕成小块,踮着脚往进料口扔。蚕宝宝们在他的“投喂”下茁壮成长,纺车吐出的丝线越来越亮,像在编织一个充满童趣与希望的未来。
阿依莎公主捧着刚织出的经纬缎样布,看着上面若隐若现的蚕宝宝爬过的痕迹,笑着对张小说:“这些痕迹像极了波斯地毯上的花纹,不如我们就用这个做新的图案吧。”张小小点头称是,目光落在朱瞻墭身上,只见他正小心翼翼地把一只蚕宝宝放在自己的手背上,咯咯地笑着,那笑声清脆悦耳,像极了纺车转动的声音。
朱高炽坐在葡萄架下,看着这温馨的一幕,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些蚕宝宝不仅织出了精美的锦缎,更织出了孩子们的快乐,织出了大明的生机与活力。他轻轻咳嗽了几声,拿起案上的奏疏,继续审阅着全国各地推广经纬车的进展。阳光透过葡萄叶的缝隙洒下来,照在他的脸上,也照在那不断转动的纺车上,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而充满希望。
七月流火时,第一批用经纬车织出的军布送到了漠北。朱高煦的回信随着大雁传来,信纸边缘沾着的沙棘汁晕染了字迹:“这布做的帐篷能防箭!让织锦学堂再送些,要绣上猛虎图案,比阿鲁台的狼旗威风。”信末还画了个龇牙的老虎,爪子下踩着团丝线,显然是照着朱瞻墭的虎头鞋画的。
张小小看着信忍不住笑,正教绣娘们给军布绣猛虎时,朱瞻墭又惹出了乱子。他趁人不备,把阿依莎的绿宝石头冠塞进了染缸,等众人发现时,那冠上的宝石己被靛蓝染成了孔雀蓝,却意外地更好看。“这叫‘锦上添花’,”张小小笑着打圆场,“波斯的绿宝石配上江南的靛蓝,像极了丝绸之路的颜色。”阿依莎看着变了色的头冠,忽然拍手道:“就用这颜色织战旗!”
秋收时节,朱棣在天坛举行了盛大的籍田礼。朱高炽亲自扶着犁,经纬缎做的礼服下摆沾着泥土,却依旧挺首了腰背。当他将第一束稻穗献给神农坛时,远处传来了织锦学堂的报喜声——用经纬车织出的桑蚕丝,竟在万国丝绸大会上得了头奖,波斯、高丽的使节都来求购织法。
“这才是真正的万国来朝。”朱棣望着坛下欢呼的百姓,忽然对朱高炽道,“比再多的胜仗都管用。”他抚摸着儿子被汗水浸湿的衣领,那里用经纬缎绣的暗纹还很挺括,“你母亲若在,定会夸你做得好。”朱高炽的眼眶忽然红了,咳嗽声里带着哽咽,却坚定地点了点头。
重阳节那天,织锦学堂的工匠们献上了幅巨大的《五谷丰登图》。整幅图用十种不同的经纬缎拼接而成,山东的棉、江南的丝、漠北的毛在阳光下交织,像幅流动的江山社稷图。朱棣亲自为这幅图揭幕,当看到图中央那台经纬车的图案时,这位征战半生的帝王忽然湿了眼眶:“这比《永乐大典》更实在,看得见,摸得着,是百姓的饭碗。”
寒风起时,东宫的暖阁里暖意融融。张小小正教阿依莎用新丝线绣《百子图》,朱瞻墭在一旁用毛笔乱涂,把每个娃娃的脸都画成了蚕宝宝,却得意地举着宣纸跑来跑去,墨汁甩得经纬缎地毯上到处都是。朱高炽坐在软榻上,翻着各地工坊的奏报,忽然指着山东的账目笑了:“你看,灾民们用经纬布换了粮食,还结余了不少,说要给瞻墭做周岁礼物。”
张小小凑过去看,只见账册上画着个歪歪扭扭的虎头鞋,旁边写着“用小皇孙玩丢的蚕茧丝织的”。她忽然想起江南的蚕桑宴,那些笑声仿佛还在耳畔回响,混着纺车的“咔嗒”声,像首永远唱不完的歌谣。
而此刻的漠北,朱高煦正穿着经纬缎做的棉甲,站在新搭建的工坊前。工匠们用他送来的沙棘纤维混纺布料,织出的马衣既防沙又保暖。他看着纺车转动的丝线,忽然觉得这比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更让人安心。“等开春了,”他对身边的亲兵说,“我们回京,看看那小子又把什么东西塞进了纺车。”
归期未定,但经纬交织的丝线早己将南北连接。东宫的纺车还在转动,织出的不仅是锦缎,更是一个个温暖的日子,在时光的长河里,绵延不绝。当第一片雪花落在织锦学堂的窗台上时,张小小忽然觉得,这深宫的岁月,就像这经纬交织的布料,有经线的坚韧,也有纬线的温柔,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织出了最动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