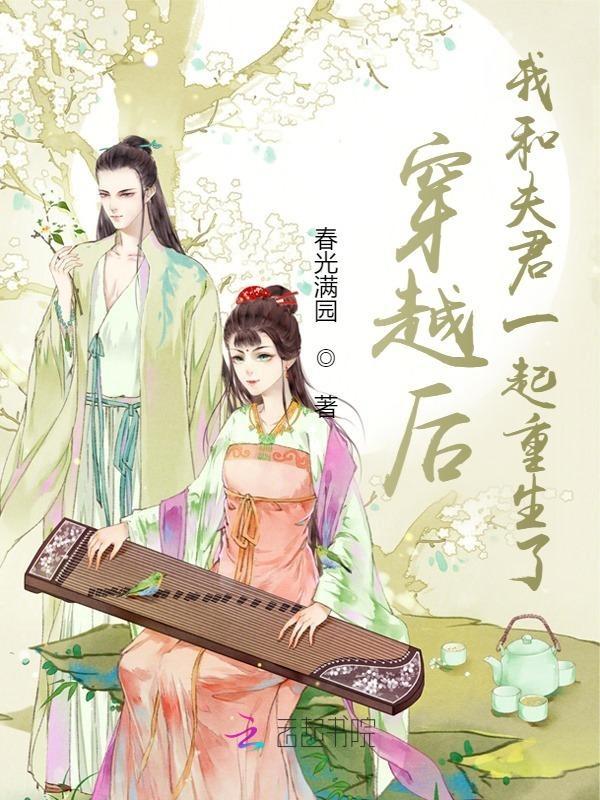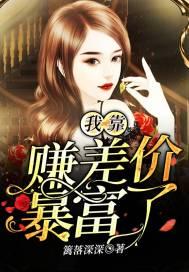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穿越成燕王txt > 第116章 春闱砚香 演武弓鸣(第1页)
第116章 春闱砚香 演武弓鸣(第1页)
永乐八年的春风裹着玉兰香掠过太液池,嫩柳抽芽的枝梢轻拂水面,将一池碧波揉碎成点点金鳞。贡院朱红高墙内,墨汁研磨的气息混着松烟墨香漫过墙头,与檐角风铃的清响纠缠着飘向天际。朱瞻基身着玄青曳撒,衣摆暗绣的云纹随着步伐若隐若现,他小心翼翼捧着朱高炽批注的《资治通鉴》,指尖着父亲苍劲的字迹,站在贡院外百年古槐下。树冠如伞,细碎的光斑在他束发的玉冠上跳跃,忽而一阵风卷起衣袂,腰间新佩的玉双鱼符显露真容——这是祖父朱棣册封皇太孙时亲赐的信物,双鱼衔尾的纹样栩栩如生,鱼鳞处银丝密镶的纹路在日光下流转,恰似太液池底被风搅动的碎银,又像是祖父眼中殷切的期许。
“这些举子要考三天三夜呢。”张小小提着描金食盒款步而来,经纬缎裙裾扫过石阶上的青苔,绣着并蒂莲的裙摆如蝶翼轻颤。她将食盒轻轻递到朱瞻基手中,掀开盒盖,阵阵甜香扑面而来,“我特意让厨房做了些绿豆糕,清热解暑。你送去给监考官,顺便学学怎么看策论,将来治国理政可少不了这些。”食盒里,绿豆糕整齐摆成“连中三元”的字样,雪白的糕体上,桂花纹是织锦学堂新刻的雕版所印,还带着淡淡的墨香。而每个糕饼上,都沾着小小的指印,那是朱瞻墭昨晚缠着张小小非要亲手印上去的,此刻仿佛在诉说着小王爷的天真烂漫。
朱瞻基刚接过食盒,就见朱高煦骑着马从街对面奔来。玄铁甲胄在晨光里泛着冷光,马鞍上搭着张刚猎的白鹿皮,毛茬上还沾着草叶。这位皇叔的战马踏着碎金般的晨晖疾驰,马蹄声如战鼓般震得石板路微微发颤。
“大侄子,不去演武场较量,在这闻墨臭味?”他翻身下马时,马蹄溅起的泥点差点弄脏朱瞻基的玉带,“昨日我部新制了批牛角弓,射程比你上次用的远三成。”朱高煦一边说着,一边豪迈地拍了拍腰间的箭囊,眼神中满是炫耀。
正说着,贡院里忽然传来喧哗。原来有举子的考卷被风刮出窗,飘落在朱高煦的马前。纸卷上的策论墨迹未干,写的正是“论郑和下西洋利弊”,末尾还画着艘歪歪扭扭的宝船,桅杆上竟缠着经纬缎的绳结。那宝船虽画得稚拙,却也能看出气势恢宏,仿佛随时要冲破纸面,驶向那波涛汹涌的大海。
朱瞻基捡起考卷时,见落款处写着“吴敬梓”,笔尖的飞白带着股倔强气。字迹刚劲有力,透露出这位举子不凡的风骨。
“此人敢说真话。”朱高炽不知何时也来了,咳嗽声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说下西洋虽扬国威,却使‘公私烦费’,当‘节用爱民’。”他指着卷上的宝船,“这桅杆画得好,像极了郑和送来的图纸,只是绳结该用双环扣,才不会打滑。”朱高炽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在空气中比划着双环扣的打法,神情专注而认真。
朱瞻基把考卷还给监考官时,特意叮嘱:“此卷用心看。”转身却被朱高煦拽着往演武场跑,玄铁甲胄的冰凉贴着他的臂弯,少年忽然想起朱棣的话:“既要懂文墨,也要识弓马。”演武场的沙地上,朱高煦己搭好箭靶,远处的旗幡用经纬缎缝制,风过时哗啦啦作响,红底金字的“太孙”二字格外醒目。
“看我的!”朱高煦扯开铁胎弓,箭矢离弦的锐响惊得场边的猎犬狂吠,却见那箭擦着靶心飞过,钉在后面的柳树上——原来朱瞻墭不知何时爬到了树杈上,正举着片柳叶当箭玩,吓得朱高煦的手一抖。“小兔崽子!”他吼声未落,朱瞻基的箭己稳稳射中靶心,箭尾的红缨在风里簌簌颤动。
“二叔这是分心了。”朱瞻基笑着收弓,掌心的薄茧又厚了些。朱高煦刚要反驳,就见乳母抱着朱瞻墭追来,小家伙手里还攥着那支射偏的箭,箭杆上的漆被啃掉一块,露出里面的桑木芯——竟是用江南的桑枝做的,柔韧性比北地的桦木还好。
春闱放榜那日,吴敬梓果然高中探花。进宫谢恩时,他捧着的谢恩折用经纬缎包着,缎面上绣的“鹿鸣”图案针脚虽糙,却透着股质朴气。“臣不善丹青,”他红着脸解释,“这是家母用织锦学堂的边角料绣的。”朱棣看着那歪歪扭扭的鹿头,忽然笑了:“把你那篇论下西洋的策论抄十遍,送东宫给皇太孙当范文。”
朱瞻基在文华殿抄录策论时,朱瞻墭正趴在他的案上捣乱。一岁多的娃娃抓起朱砂笔,在“节用爱民”西字上画了个圈,嘴里还咿咿呀呀的,像是在批注。张小小进来时,见兄弟俩满脸墨痕,活像两只刚从墨池里爬出来的小猫,忍不住笑道:“这要是让御史看见,又要参奏太孙玩忽职守了。”
暮春的雨打湿了织锦学堂的窗棂,张小小正教吴敬梓的母亲改良经纬缎的染色技法。“用苏木煮的水染经,紫草煮的水染纬,”她指着晾晒的样布,“这样织出来的料子,从不同角度看会变色,像极了太孙的玉双鱼符。”老妇人啧啧称奇,手里的纺锤转得飞快,纱线在雨雾里闪得像银丝。
消息传到漠北时,朱高煦正围着篝火烤鹿肉。听传令兵说朱瞻基的策论被朱棣夸奖,他忽然把啃剩的骨头往火里一扔:“这小子,笔墨功夫见长,骑射可别落下。”他从箭囊里抽出支雕翎箭,在火光下刻下“秋猎”二字,“告诉太孙,重阳节的围猎,我要他猎只比这白鹿还大的熊。”
东宫的暖阁里,朱瞻基把朱高煦的箭摆在案头,与吴敬梓的策论并排。窗外的雨停了,晚霞透过云层,在箭杆上的“秋猎”二字镀上金边。他忽然拿起笔,在策论的空白处写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如经纬交织,方为正道。”墨迹未干,朱瞻墭又爬过来,在旁边画了个举着弓箭的胖娃娃,箭头还指着只歪歪扭扭的蚕宝宝。
张小小看着这父子三人的笔迹——朱高炽的温润,朱瞻基的锐意,朱瞻墭的天真,忽然觉得这暖阁里的时光,就像那经纬交织的绸缎,将严肃的国事与琐碎的亲情,都织成了最动人的篇章。而檐角的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像是在为这平淡又温馨的日子伴奏。
七月流火,科举的余热还未散去,朱瞻基己开始跟着朱高炽处理一些简单的政务。这天,他正在审阅各地上报的灾情奏折,忽然被一份来自山东的奏报吸引。上面说当地遭遇了罕见的蝗灾,庄稼损失惨重。朱瞻基眉头紧锁,想起张小小教他的“民为邦本”,立刻起身想去见朱棣。
刚走到宫门口,就碰到了朱高煦。朱高煦肩上扛着一把刚打磨好的大刀,见朱瞻基神色凝重,便问道:“大侄子,何事如此着急?”朱瞻基把山东蝗灾的事一说,朱高煦满不在乎地说:“这点小事,派些士兵去灭蝗就是了。”朱瞻基摇摇头:“二叔,蝗灾凶猛,单靠士兵不够,还需组织百姓,传授他们有效的灭蝗方法。”朱高煦愣了一下,随即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全,我这就去调兵,你负责制定灭蝗的法子。”
两人分工合作,朱瞻基查阅《永乐大典》中关于灭蝗的记载,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详细的方案,包括如何挖沟掩埋蝗虫卵、如何用烟雾驱赶成虫等。朱高煦则迅速调集兵力,奔赴山东。很快,山东的蝗灾得到了控制,百姓们纷纷称赞皇太孙聪慧过人。
朱棣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在朝堂上对朱瞻基大加赞赏:“皇太孙年纪虽轻,却有如此见识和担当,将来必成大器。”朱瞻基谦虚地说:“此乃父皇教导有方,二叔鼎力相助,孙儿不敢居功。”满朝文武见状,都为大明有这样的继承人而感到欣慰。
秋高气爽,重阳节的围猎如期而至。朱瞻基骑着一匹矫健的骏马,身着劲装,英姿飒爽。朱高煦早己在猎场等候,见朱瞻基来了,便扬声道:“大侄子,准备好了吗?今天咱们一较高下。”朱瞻基微微一笑:“二叔,请指教。”
围猎场上号角声破空而起,朱瞻基双腿轻夹马腹,枣红马如离弦之箭窜入密林。他身姿如松,手中雕弓拉成满月,箭矢破空时精准钉入野兔后腿,那猎物在枯叶堆里扑腾两下便没了动静。朱高煦的黑马紧跟其后,弯刀寒光一闪,竟生生将野猪脖颈劈出半尺深的伤口,温热的血溅在他玄色箭袖上,晕开大片暗红。
猎场中央陡然腾起黑影,朱瞻基眯起眼睛锁定目标——那只金雕正展开丈余长的羽翼,利爪下还擒着只仓皇的山雀。他抽出三支连珠箭,箭矢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第一箭惊得金雕骤然拔高,第二箭擦着尾羽掠过,第三箭却穿透左翼。金雕哀鸣着坠落,掀起一片尘烟。
"好小子,有你的!二叔认输了。"朱高煦的手掌重重拍在朱瞻基背上,却难掩眼底赞赏。远处朱高炽由侍卫搀扶着走来,轮椅碾过碎石的声响惊动了正在追蝴蝶的朱瞻墭,小世子举着沾满草屑的网兜扑进父亲怀里,惹得众人忍俊不禁。
暮色将天边染成蜜色,篝火上架着的鹿肉滋滋冒油,张小小掀开食盒,露出撒着桂花的豌豆黄。朱高炽颤巍巍地将烤好的兔腿分给两个儿子,烛火映着他苍白的面庞,眼中却盛满笑意:"瞻基的箭术愈发精进,煦弟的勇武也不减当年。"
朱瞻基倚着树干,看着弟弟在月光下追逐流萤的身影,又望向远处举杯相谈的二叔和父亲。夜风送来烤肉的香气,混着张小小身上淡淡的皂角味。他着腰间玉佩,那是皇祖父赐下的随身之物,冰凉触感却抵不过此刻掌心的温热。远处紫禁城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他望着漫天星斗,忽然觉得肩头的重担也变得坚实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