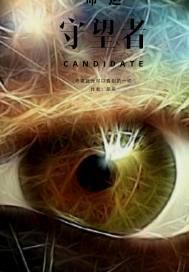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印度有法律吗 > 第16章 辽使夜奔(第3页)
第16章 辽使夜奔(第3页)
夜幕低垂,章衡的马队悄然出城,沿着官道飞驰,首奔幽州。马蹄踏在冰面上,发出清脆的“嘚嘚”声,像是踩在凝固的月光上。
幽州城,辽国的边陲重镇,城墙高耸入云,城楼上旗帜猎猎作响,尽是铁浮屠与狼牙棒的影子。章衡的马队在城门外停下,他未着甲胄,仅穿一袭深色长袍,腰间悬银鱼袋,身后只跟了霍山与两名皇城司亲信。
“大宋使者到。”霍山高声通报,声音在夜色中格外清脆。
城门“嘎吱”打开,幽州守将萧忽古亲自出迎。他身披重铠,腰悬弯刀,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章少监,深夜到访,莫非是来为耶律大人收尸的?”
章衡下马,拱手为礼:“萧将军说笑了。在下此行,是为两国边境的安稳而来。”
萧忽古冷哼一声:“边境安稳?耶律仁先私运火药铜铁,意图何在?若非我及时截下,幽州怕是要成火药桶了。”
章衡不动声色:“将军所言极是。但耶律仁先毕竟是大辽使者,若他死在幽州,只怕两国边境要起风云。”
萧忽古目光如刀:“他伤势沉重,命不久矣。章少监若真忧心边境,不如替我辽国除掉这个祸根。”
章衡心中一凛,面上却带笑:“萧将军此言差矣。耶律仁先虽有不是,但大辽国体为重。将军既握幽州兵权,当知唇亡齿寒之理。”
萧忽古被噎得一滞,转身引章衡入城。城内火把通明,耶律仁先被安置在东门箭楼,裹着一层又一层的厚毡,却仍止不住发抖。他右肩中了一箭,左腿被刀砍伤,血虽止住,人己虚弱得不成样子。
“宋人……你们竟敢来?”耶律仁先见章衡,咬牙切齿。
章衡上前一步,手里不知何时多了副银针。他轻轻一挑,银针没入耶律仁先肩头,血珠沁出,箭伤处竟泛起一丝红晕。
“章某虽是宋人,却也是行医之人。”章衡轻声说,“此针可续筋骨,止痛续命。耶律大人若不想死,便听在下一言。”
耶律仁先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想起数日前的崇政殿,想起火雨流星铳的惊雷,想起自己在宋使面前的落败,心中恨意如潮水般汹涌。
“宋人……你们的火器……”他艰难开口。
章衡点头:“正是火器。耶律大人可知,若非大辽内乱,这火器早己列装边军,燕云十六州怕也早己物归原主。”
耶律仁先身子一震,眼中掠过一丝惊恐:“你……你想怎样?”
章衡俯身,靠近耶律仁先耳边,声音低得像蛇信子扫过:“我想怎样?耶律大人,你我皆是乱世之人,有些事,点到即止。”
他起身,拍了拍耶律仁先肩头的厚毡:“好好养伤,待辽主问起,就说大宋的火器,是天命所归。”
走出箭楼,夜风卷着血腥气扑面而来。萧忽古站在不远处,见章衡出来,抱拳道:“如何?”
章衡摇头:“耶律仁先伤重,怕是活不过明日寅时。将军,你这幽州,可要准备好接大辽的怒火了。”
萧忽古冷哼:“怒火?耶律仁先一死,大辽朝堂必乱。我萧忽古虽不如他得宠,却也不是易与之辈。”
章衡点头:“那就好。在下告辞,还望将军保重。”
马队再次启程,幽州城墙在夜色中渐渐远去。章衡回头,望向箭楼方向,那里一灯如豆,为耶律仁先守着最后的时光。
“天命所归……”他轻声重复,声音在风中消散,如同一声长长的叹息。
三月廿九,寅时三刻,耶律仁先薨于幽州箭楼。辽国以“病逝”为由,秘不发丧,萧忽古接掌使团,仓皇北返。
大宋朝堂,因这一连串变故,暂且按兵不动。赵祯闻报,只淡淡说了句:“天意。”
章衡回京后,火器监的进度一日千里。皇城司暗中将辽使夜奔、幽州刺杀、耶律仁先之死连成一线,编成话本,在汴梁城传得沸沸扬扬。民间皆道:“辽使夜奔,天火降灾;耶律暴毙,幽州失守。”一时间,大宋民心大振,边境守军也因这传闻士气高涨。
而这一切,章衡只是微微一笑,将那卷《火器利弊策》重新卷起,收入匣中。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火器之路,仍有许多风雨。
西月将至,春寒料峭,可章衡的心中,却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照亮了未来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