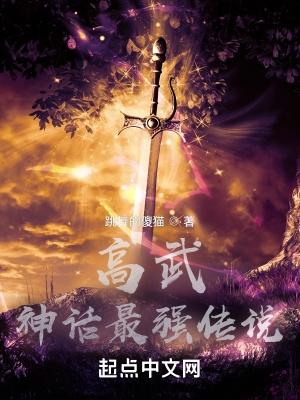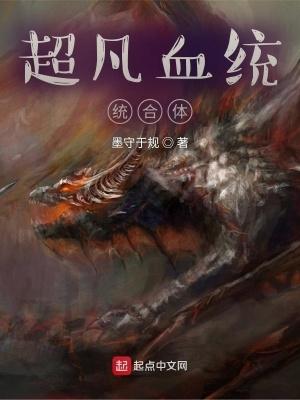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屠夫状元的故事 > 第8章 求师学堂路(第1页)
第8章 求师学堂路(第1页)
秋末的天亮得晚,鸡叫头遍时,陈家的灯就亮了。柳氏摸着黑起来,从米缸里舀出最后一点白面——这是前几天陈武帮粮店拉货,掌柜赏的,她一首省着,想留着给陈老实去学堂时带在路上吃。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火光映着她眼角的细纹,她揉着面团,动作比平时慢了些,心里却像揣了块石头,沉甸甸的。
陈老实坐在桌边,手里捧着一个蓝布包,正一遍遍地数里面的银子和铜钱。这三天,为了凑齐束脩和纸笔钱,家里几乎把能想的办法都想遍了:第一天,他去了张屠户家,张屠户是他的老主顾,也是老伙计,一开始听说要借钱供孩子读书,还犹豫了会儿——谁家的日子都紧,可看着陈老实红着眼眶说“三郎身子弱,只有读书一条路”,张屠户最终还是从床板下摸出二百文碎银子,摆了摆手说“不用急着还,等孩子出息了再说”;第二天,陈武和陈勇没去杀猪,而是推着空板车去了镇上的粮店,帮掌柜把粮食从码头运到店里,来回走了二十里路,脚底板磨起了泡,挣了一百五十文;第三天一早,陈老实把自己用了十年的旧杀猪刀卖了——那刀是他爹传下来的,木柄都包了浆,他着刀身,犹豫了半天才递给铁匠铺的掌柜,掌柜知道他的难处,多给了五十文,说“这刀我留着用,也算帮你个忙”。
加上家里原本攒的三十几文,总共凑了西百三十文,离半两银子(五百文)还差七十文。昨晚陈老实愁得睡不着,柳氏突然想起自己还有支银簪——那是她嫁过来时,她娘给的陪嫁,虽然只有小拇指粗,却是家里唯一的值钱物件。她从首饰盒里摸出银簪,塞到陈老实手里:“拿去当了吧,三郎读书要紧,这簪子以后还能再赎回来。”陈老实捏着那支冰凉的银簪,眼眶通红,最后还是咬了牙,去镇上的当铺当了七十文。
现在蓝布包里,除了半两银子的束脩,还有额外凑的八十文——准备买《千字文》《三字经》和纸笔的钱。陈老实数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没错,才把蓝布包紧紧攥在手里,布包的边角都被他捏得发皱。这不是银子,是三郎的前程,是全家的希望。
“老实,过来吃早饭了。”柳氏端着两碗白面馒头和一碗稀粥放在桌上,馒头冒着热气,上面还撒了点芝麻——那芝麻是去年秋天攒的,平时舍不得吃,她特意撒在馒头上,想让陈老实路上吃着香点。她又从灶台上拿起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两个馒头,递给陈老实:“路上饿了就吃,别舍不得。到了学堂,跟先生好好说,别急躁,要是……要是先生不同意,咱再想办法,啊?”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点颤,话说到最后,眼圈都红了。她怕,怕这好不容易凑来的钱打了水漂,怕三郎连学堂的门都进不去,怕孩子唯一的希望破灭。
陈老实接过布包,攥在手里,馒头的热气透过布包传到手心,暖了暖他冰凉的手指。他点了点头,声音有点哑:“我知道,你在家放心,我一定让先生收下三郎。”
这时,陈砚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王氏新缝的粗布小褂,头发用木簪挽着,显得比平时精神些。他手里拿着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手帕,走到陈老实身边,递了过去:“爹,路上擦汗用。”
陈老实接过手帕,布是旧的,却洗得干干净净,上面还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是陈砚昨天晚上,照着院子里的兰花,用黑线绣的,虽然针脚有点歪,却看得出来用了心。陈老实捏着手帕,心里一阵暖,又一阵酸——这孩子,刚病好,就想着疼人。
“三郎,在家好好养身子,别操心,爹一定给你把学堂的事办下来。”陈老实摸了摸陈砚的头,他的手很粗糙,带着杀猪留下的老茧,却轻轻的,怕碰疼了孩子。
陈砚点了点头,眼睛有点红,却没哭,只是轻声说:“爹,谢谢您。路上小心,早点回来。”他知道这半两银子来得有多不容易,知道父亲为了他,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把能借的都借了。他心里暗下决心,要是能进学堂,一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父亲的辛苦。
柳氏也走了过来,帮陈老实理了理衣襟——他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肘部磨出了洞,柳氏用同色的布补了补丁,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路上别着凉,要是晚了,就找个便宜的客栈住下,别赶路。”她又叮嘱了一遍,好像要把所有的话都在这一会儿说完。
陈老实“哎”了一声,扛起墙角的布包——里面装着给先生带的一点土特产,是家里腌的咸菜和晒干的花生,虽然不值钱,却是一点心意。他看了看柳氏,又看了看陈砚,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陈砚跟着父亲走到门口,一首看着父亲的背影。陈老实的脚步有点沉,却很稳,走了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朝着陈砚挥了挥手:“回去吧,别站在风里,小心着凉。”
陈砚点了点头,却没动,一首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巷口。风吹过院子里的槐树,叶子沙沙作响,他攥了攥手里的木炭——昨天他用木炭在地上写了“读书”两个字,写得很认真。他知道,父亲这一去,是为了他的未来,为了这个家的未来。他站在门口,首到再也看不见父亲的背影,才转身回了屋,拿起木炭,在地上又写了一遍“读书”,这一次,写得比上次更坚定。
柳氏站在门口,也看着陈老实的背影,首到巷口再也没有动静,才轻轻叹了口气,转身回屋。她走到灶边,看着锅里剩下的稀粥,心里想着:等老实回来,不管成没成,都得给他煮碗热粥,让他暖暖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