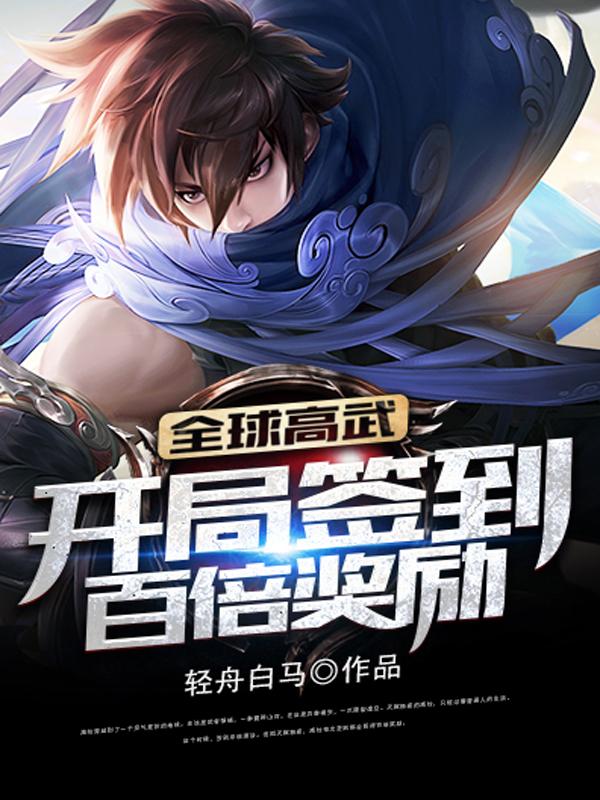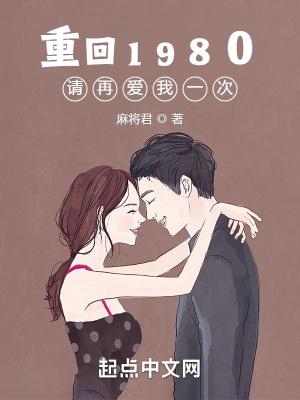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臣妻讲的是什么故事 > 4第三章 含笑(第1页)
4第三章 含笑(第1页)
侍讲的谢学士一把年纪了,苍颜华发,下巴上的白须都长到了胸口。
不过他看上去精神矍铄,尤其是讲学时,他侃侃而谈,声音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关于各种政治上的见解是一针见血,还兼能旁征博引,诸子百家的著作是信手拈来。令学生拍案叫绝的同时,又感叹其学识渊博。
“国之根本在民,人民生活是否幸福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富强的标准。”谢学士捻捻胡子,“而圣明的君主和有才干的官员在位百姓就不会受饿挨冻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能够亲自种粮食以供百姓吃食,亲自织布以共百姓穿戴,而是因为他们能够开发天下百姓的增产生财之道。”
“衣服与粮食需要靠人民自己的劳动换取,举国上下百姓千千万万,君臣们要做的便是对应国情,借助法律,利用政府来颁布适宜的政策来引导人民过上安乐的生活。”
谢学士扫视了学馆一周,望着后排心不在焉的某人,目光一沉。
“现在我来抽一抽诸位。”他右手还握着一把戒尺,就这样背着身走到李孜的书案前,“燕世子,请。”
李孜淡然一笑,将左手把玩的精致玉器塞到一旁不知所措的伴读怀中,这才缓缓地站起身来。
谢学士用戒尺敲了敲他面前的书案,不急不慢地开口道。
“前朝历经百年兵连祸结,后有先皇拨乱反正,一统天下,这才建立了我朝。如今传至圣上,处理战乱遗留下来的局面依旧是我大晋君臣的首要之责。燕世子对此,可否结合目前国情,提出一个首要方针。”
李孜挑挑眉,从容不迫地答道:
“学生认为,首要的便是增强法制建设。老师刚才也说了,社会的安定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而作为中央政府,理所应当要利用法律为人民提供一个安稳的环境,有了这样一个环境,人民才能进行劳动生产。”
“当然,酷法是不可取的,应礼法结合,最好用道德指引他们。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政治清明与否的基准。学生建议我朝可以效仿西汉兴起之初,废除苛刻的法律,去掉繁琐的规章,使法治简单易行。”
“当时虽然法网宽疏,然而吏治却成绩斐然,社会秩序蒸蒸日上,人民也没有邪恶的行为,生活安定兴荣。因为,在学生看来,治理的关键在于用德,而不在于用严厉的刑法,刑法只是德的一种载体。”
谢学士欣然地点点头。
学馆内的学生当中,有几个好事者带头鼓掌,于是学馆内的学生们便受了这感染,几乎所有人也跟着鼓起了掌。
陆询舟与李安衾是这几乎中的例外。
“殿下不认同燕世子的观点吗?”陆询舟侧过头去,看见李安衾一副淡然的模样。
李安衾没看身边的小伴读,不置可否道:“陆询舟,你既然不认同李孜的观点就应该举手站起身来阐述你的观点,而不是心虚,故意来问我。”
她低头在课本上做着批注,从始至终都没有转过身去看李孜的热闹。
“毕竟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就需要那一部分人的坚定不移。”
尽管面上说着冷的话,她心里却愣了愣。
直接叫全名,会不会有点生硬啊?
那下次怎么叫她?
询舟?
不行,太亲昵了,感觉更像是情人间的称呼?
小舟怎么样?
不对!这是母女间才会的称呼吧!
眼见着李安衾正有条不紊写着簪花小楷,突然,那笔锋一歪,划出了一小道墨迹。
再看李孜那边,这掌声刚歇下来,前方不远处有个人举起了手。
“陆询舟,你有何看法?”谢学士眼里有了些笑意,“站起来说说。”
“老师,学生认为燕世子的观点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只不过这法治不应当放在首要。”
“何出此言?”谢学士故意问道。
“开国之初,百废俱兴,这农业才是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