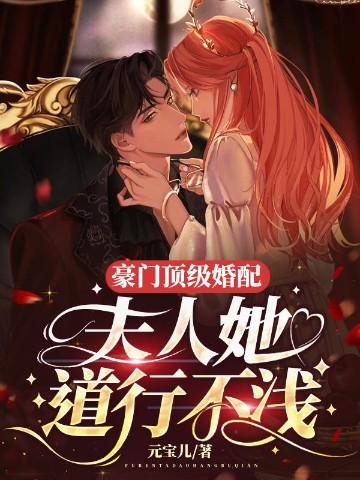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桥中无人修 > 第5章 归魂河的旧约(第1页)
第5章 归魂河的旧约(第1页)
天光从灰白渐渐泛亮,寒河镇的雪还在下。夜里的怪梦仿佛被这无休无止的雪掩盖,但沉在心底的那道黄光,却怎么也被抹不掉。
李砚被老人推醒时,炉火己经只剩下暗红的余烬。屋外,风小了,天地间只余细碎的雪沫在空气中游移。老人披着厚棉衣,将那只昨夜发光的木匣用层层布包裹好,塞进一个黑布袋,拉紧系扣。
“走吧,我送你回去。”
旧木门吱呀一声推开,清晨的冷意带着一种河水特有的腥潮味涌进来。李砚不自觉地朝河桥方向望了一眼——远处雾气笼罩,寒河桥的轮廓模糊成一道影子,像是悬在空中的断裂栈道。
一路无言。雪在脚底发出细碎的“咯吱”声,像踩在厚厚的棉被上,又像踩在一层薄薄的骨头上。
快到家门口时,母亲的身影突然从门内闪出,她穿着厚棉袄,却没有裹围巾,说话的声音带着急促的颤音:“你去哪了?!”
李砚还没来得及答,老人上前一步,“娃子昨夜差点冻坏,是我捡回来的。”
母亲的目光警惕地在两人之间逡巡,最后落在老人的眼上,神色微微一变——那种变化极细,细到李砚差点怀疑自己看错了。
“你先进屋,我和他聊几句。”母亲语气中透着生硬的命令。
李砚犹豫了一下,走进院子,关上门时,他回头——雪雾之中,母亲和老人站得很近,头微微低着,不知道在说什么,偶尔瞥来的眼神里,藏着他读不懂的密意。
屋内的灶火己经烧旺,土豆炖腊肉的香味在锅盖边沿溢出。母亲回来的时候,脸色比早晨还要苍白。
“以后不许再去桥那边。”她把湿雪拍落,脱下棉袄在火旁烤,“记住,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李砚忍不住问。
母亲抬眼看了看他,像是在斟酌着什么,最后只是摇头,“知道得越多,越不安生。”
李砚想起昨夜老人提到的“渡魂灯”,又想到他口中的“归魂河”,忍不住追问:“是不是和河有关?是不是桥下——”
“吃饭!”母亲打断他,语调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硬冷。
汤勺击在碗边的清脆声,像是冰面上的裂痕一点点蔓延,他甚至可以在脑子里看到那片冰下的黄光在脉动。
午后,雪暂歇,李砚悄悄出了门。
寒河镇白日的街道静得出奇,积雪没到脚踝,踩下去后会冒出一丝冰凉的雾气。沿着镇子通往河滩的小路走,他看到河面结着厚厚的冰,表层覆了一层雪,几乎看不出昨夜他曾跌倒、被救起的痕迹。
只有桥墩的位置,冰色微微发暗,像是被河底的什么在反复撞击。
“在找什么?”
声音从背后响起,李砚猛一转身——是老人。他不知何时站在雪地里,脚下没有留下任何来时的脚印,像是凭空出现。
“我……只是看看白天的河。”李砚支吾。
老人望着桥,“河白天安分,夜里才有性子。天要换了,节气一到——契约也就到了。”
“契约?”
老人缓缓踱到桥边,半眯起眼,“归魂河和镇子之间,有个旧约。每到冰消前的一个夜晚,要渡一盏灯下水,送走那些不甘心的魂——不送,河会自己来取。”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以前,都是我们这些守灯人来渡。你父亲那年——有人想破坏旧约,结果……”
结果没有说完,但李砚的心口己经隐隐发紧。
“既然有约,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知道?”
“知道的人越多,灯就越找得到人。”老人凝视着他,“归魂河的灯,不挑死活,只挑缘分。”
雪又开始飘,几片落在老人的棉帽上,很快融成了水珠,顺着脸纹滑落,看上去就像是一滴滴冰凉的泪。
傍晚回到家,母亲正在院里烧一炉奇怪的香,香是暗红色的条状物,燃烧时冒出的烟有淡淡的甜味,又带着刺鼻的辛辣。
“闻到香味,就别出屋。”她看着李砚,神情说不出的凝重,“今晚谁叫你,你都不能应声。”
雪夜悄然降临。李砚躺在床上,房梁上挂着的风铃在没有风的时候诡异地轻轻颤,发出比白日更尖细的音色。
他几乎可以听见,窗外、远处的河面下,有光在凝聚——一呼一吸之间,把他的脉搏牵得越来越快。
那光,似乎还带着熟悉的气息。
然后,耳边再次响起了那个声音:
“下来……灯等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