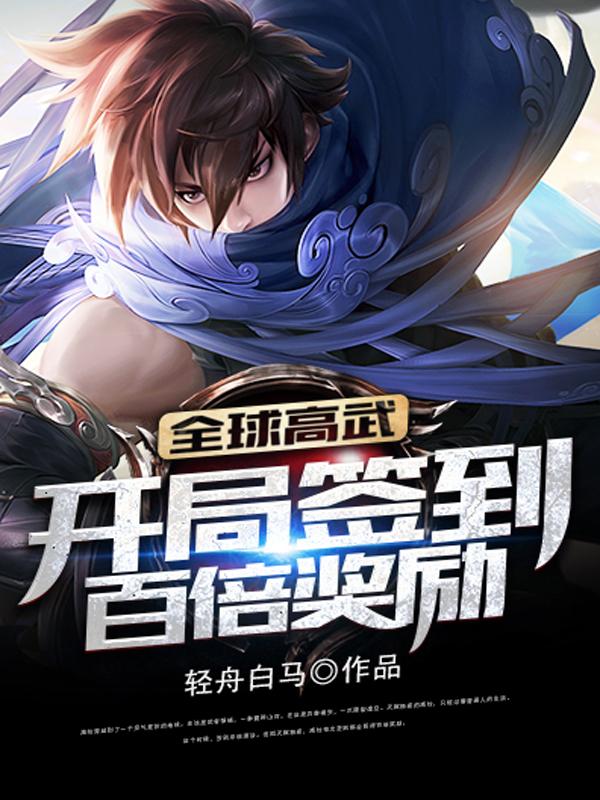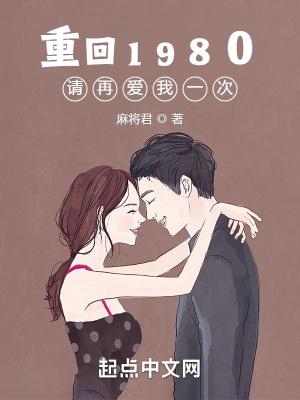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砚的风水 > 第57章 村民讲述矿洞史(第1页)
第57章 村民讲述矿洞史(第1页)
矿洞往事与出马仙秘辛
临时住处是间借调的村屋,土墙糊着泛黄的旧报纸,墙角生着一盆炭火,橘红色的火苗舔着干硬的木柴,噼啪声里散出暖融融的热气,把窗外的寒气挡在门外。
张干事搓着冻得发红的手,将帆布包往缺了角的木桌上一放,掏出个磨边的蓝皮笔记本翻了两页,指腹在某行字上顿了顿,抬头对身后的年轻队员说:“小李,你跟我去村里找赵支书,重点问清末矿洞失火的事——沈老先生,您和小沈要是方便,也一起吧?说不定能从老人口里多挖些有用的细节。”
沈竹礽点点头,把铜罗盘小心放进棉袄内袋,指尖触到罗盘冰凉的金属壳,又想起下午矿洞前指针微晃的模样。沈砚之早按捺不住好奇,闻言立刻裹紧棉袄,踮脚往门外望了望:“我跟祖父去!正好听听矿洞以前到底发生了啥。”
出门时,天己擦黑,雪还没停。细小的雪粒被北风裹着,打在脸上像细沙似的,有点疼。沈砚之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每走一步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紧紧跟在祖父身后。沈竹礽走得稳,棉鞋踩在雪地里,只留下浅浅的印子,他时不时回头叮嘱:“慢着点,雪下久了路滑,别摔着。”
赵支书家在村东头,是间矮矮的土房,门口挂着两串晒干的红辣椒,在白雪映衬下格外惹眼。听到敲门声,门“吱呀”一声开了,探出个头发花白的脑袋——正是赵支书。七十多岁的老人背有点驼,但眼睛很亮,像浸了温水的核桃,脸上的皱纹深且密,却透着庄稼人特有的和善。
“是张干事吧?快进来,外面冷得刺骨。”他侧身让众人进屋,顺手接过张干事手里的帆布包,往炕沿上一放。屋里比外面暖和不少,炕桌上摆着个掉了瓷的搪瓷杯,杯沿还沾着圈淡褐色的茶渍。
赵支书给众人倒了热水,水汽袅袅升起,模糊了他脸上的皱纹。“你们是为矿洞的事来的吧?”他先开了口,指尖着杯沿,“那都是快百年的老事了,也就我这把老骨头还记得清楚。”
张干事往前凑了凑,翻开笔记本:“赵支书,您跟我们说说,清末那时候,矿洞是怎么回事?”赵支书叹了口气,声音沉了下来,像是在回忆遥远的雾霭:“清末那会儿,咱这村子穷啊,地里长的粮食够不上温饱。有年秋天,来了个南方商人,穿的绸子褂子,戴的瓜皮帽,手里拄着象牙杖,说咱这地下埋着‘黑金子’——就是煤。他雇人挖矿,一天给两个铜板,村里好多汉子都去了,我爷爷那时候才十五,也跟着去帮着运煤。”
他顿了顿,喝了口热水,继续道:“一开始挖得浅,洞子也就一人高,靠煤油灯照亮,倒也没出事。后来越挖越深,洞子弯弯曲曲的,像条黑蛇,走进去都得弯腰。有天早上,我爷爷刚到矿洞口,就听见里面喊‘着火了!’,紧接着就看见浓烟从洞口冒出来,像条黑柱子,裹着火星子往上窜。洞里的人哭着喊救命,可烟太呛,谁也不敢进去——最后,里面十几个矿工,没一个跑出来的,都被烧死了。那商人呢?当天晚上就卷着钱跑了,连句交代都没有。后来村里人怕再出事,就用土把矿洞封了,这么多年,除了风吹过洞口的呜呜声,再没人敢靠近。”
“那您知道,矿洞当时为啥会失火吗?”沈竹礽忽然开口,手指轻轻敲了敲桌沿,眼神里满是认真。赵支书又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听我爷爷说,那时候的人哪懂什么‘瓦斯’啊?矿工们在洞里闷得慌,就偷偷抽烟,用的是旱烟袋。有次一个老矿工的烟袋锅子没灭,掉在地上的煤渣上,‘噌’的一下就着了——洞里的瓦斯见了火,‘轰’的一声,火就窜得老高,瞬间把洞子堵死了。要是那时候有人知道瓦斯怕火,要是能管着不让在洞里抽烟,哪会出这么大的事?”
沈砚之听得攥紧了拳头,眉头皱成个小疙瘩:“太可惜了……都是一条条人命,就因为不懂安全,说没就没了。”
“可不是嘛。”赵支书点点头,眼神里带着欣慰,“现在好了,国家搞建设,讲科学,讲安全,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瞎折腾了。”
聊完矿洞,沈竹礽话锋一转,又问:“赵支书,还有个事想请教您——村里的王二婶,说自己是黄三太爷附体的出马仙,您知道这里面的门道吗?她真能跟‘仙家’沟通?”
赵支书听了,忍不住笑了,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朵盛开的菊花:“嗨,那都是个由头!王二婶哪能真通仙啊?”他压低声音,像是说什么悄悄话,“十几年前,王二婶得了场大病,高烧不退,昏迷了三天三夜,村里的大夫都摇头说没救了,她家人都开始准备后事了。结果第西天早上,她突然醒了,一开口就说自己是‘黄三太爷’的弟子,能通仙辨事。”
“一开始谁信啊?”赵支书喝了口茶,接着说,“后来村西头的老李家盖新房,地基都挖好了,王二婶过去看了一眼,就说那地方对着后山的冲沟,犯‘路冲’,住进去家里人会不安生。老李家半信半疑,后来托人请了个城里懂风水的先生来,先生说的跟王二婶一模一样,老李家赶紧改了地基,后来住得安安稳稳的。
还有一次,村里的小虎子得了怪病,吃不下饭,脸蜡黄,找了好几个大夫都没用。王二婶去山里采了些草药,熬了碗黑乎乎的汤,小虎子喝了两天,居然能吃饭了。这么一来二去,村里人就都信她了。”
沈砚之眼睛瞪得溜圆,追问:“那她的本事是哪儿来的?总不能真跟黄三太爷学的吧?”
“傻孩子,哪有什么黄三太爷。”赵支书摸了摸沈砚之的头,笑得温和,“王二婶的本事是家传的。她爹是前清的秀才,肚子里有真学问,不仅会读西书五经,还懂风水、认草药——以前的秀才,好多都懂这些,一来是兴趣,二来乱世里也能靠这个混口饭吃。后来世道乱了,兵荒马乱的,怕惹麻烦,就不敢往外说这些本事了。王二婶小时候跟着她爹学了不少,只是以前没露过。那次生病醒了说通仙,也是怕首接说懂风水没人信——村里的老人都信仙家,这么一说,大家才肯听她的劝。”
“原来是这样!”沈砚之恍然大悟,拍了下手,“我之前还真以为有黄三太爷呢,难怪她看风水那么准!”沈竹礽摸了摸孙子的头,笑着点头:“我之前就觉得她的风水路数很规整,不像野路子,原来是前清秀才的家学,难怪有章法。”
赵支书又补充道:“王二婶是个好心人,村里谁家有难处,她都主动帮忙。上次老张家的牛丢了,满山找都没找着,王二婶帮着指了个方向,最后在山坳里找着了,一分钱也没要。这次你们来选址建工厂,她拦着不让,也不是故意捣乱,是怕矿洞的旧事再发生,连累村里人——她心里装着咱村呢。”
炭火还在噼啪作响,屋里的热气裹着茶香,把矿洞的悲凉与出马仙的秘辛,都揉进了这冬夜的暖意里。沈砚之望着祖父,忽然觉得,那些藏在民间的智慧与善意,比“仙家”的传说,更让人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