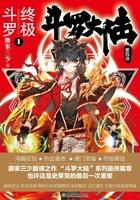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书法家砚田的个人介绍 > 第62章 二婶揭秘出马实(第1页)
第62章 二婶揭秘出马实(第1页)
砖房里的传承
出了工厂选址的空地,往西北走二里地便是王二婶住的李家村。土路被前些天的雨润得松软,踩上去没什么尘土,两旁的玉米刚抽了嫩穗,青绿色的叶片在风里轻轻晃着,偶尔有几声鸡鸣从村口的矮房里飘出来,比工地上的机器声多了几分妥帖的烟火气。
沈竹礽牵着沈砚之的手,脚步不自觉慢了些——自从确定了工厂地址,这几日净是和村干部、工程师讨论地质、规划,难得有这样清净的时刻。
王二婶走在前面,蓝布衫的衣角扫过路边的狗尾草,回头时眼角的皱纹挤成了笑纹:“俺家就这点好,偏,清净,说话也不被人打断。”
沈砚之好奇地盯着路边的土坯房,有的墙上还刷着“农业学大寨”的白漆标语,心里忍不住犯嘀咕:二婶说家是“简陋砖房”,可这村里多是土坯房,难不成砖房在这儿算讲究的?
转过一道爬满牵牛花的矮墙,王二婶的院子就到了。院墙是用碎砖垒的,没垒到顶,紫的、粉的牵牛花顺着砖缝往上爬,开得热热闹闹。院子里摆着个缺口的旧木盆,里面泡着刚从后园摘的青菜,水珠还挂在菜叶上;旁边的压水井擦得锃亮,铁制的泵杆上连一点锈迹都寻不见,一看就是日日打理的。
“快进来,别晒着!”王二婶推开木门,“吱呀”一声,屋里的光线先漏了出来。砖房确实简陋,红砖裸着墙,没刷石灰,可每一块砖都擦得发亮,连墙角的蛛网都寻不见。靠东墙摆着张老松木八仙桌,桌面被磨得泛着温润的光,两边的靠背椅上,各垫着块碎布拼的椅垫,针脚整整齐齐,一看就是手巧人做的。
最惹眼的是西墙——墙上钉着两块旧木板,绷着两张图:左边的《天文图》是宣纸的,边缘泛着黄,淡墨画的周天星宿里,朱红圆点标出了二十八宿的位置,连星宿间的连线都画得笔首;右边的《风水图》是粗布的,山川河流用墨线勾着,不同颜色的细线标着地脉走向,角落还盖着个模糊的红印,隐约能看出“钦天监”三个字。
“坐,俺给你们泡点茶。”王二婶说着,从桌下拎出个锡制的茶叶罐,打开时飘出股淡淡的炒青香。她又取来三个粗瓷碗,碗沿虽有个小缺口,却洗得干干净净。压水井“吱呀吱呀”响了几声,清凌凌的水注进铁壶,架在墙角的煤炉上——煤炉里的火很旺,没一会儿就听见壶水“咕嘟”冒泡。
等水开的工夫,王二婶指尖着茶叶罐的边缘,忽然开口:“其实‘出马仙’那套,不是俺真信有啥‘仙家’,是用来护着自己、护着学问的法子。”
沈竹礽抬眼,看见她眼神沉了沉,像是落了些旧时光的影子,“民国那时候,世道乱得很啊——兵荒马乱的不说,后来又有人抓懂风水的,说那是‘封建迷信’,抓去了就批斗,有的还被拉去给军阀看坟地,看完了就没个好下场。俺爷爷以前也是懂这个的,有回帮邻村看宅基地,被人举报了,连夜揣着这两张图躲进山里,才没被抓着。后来他就教俺,对外说自己是‘出马仙’,借‘仙家托梦’的名义看风水,这样既没人敢随便找事,学问也能传下来。”
她顿了顿,给铁壶提了提火:“你们别瞧东北‘出马仙’多,其实好多都是民间的智者——懂看地脉的风水,懂认草药治小病,还懂看星相辨时节,就是怕惹祸,才用‘仙家’的名头遮着。就像俺隔壁的张大爷,对外说自己是‘黄仙’上身,其实他能辨出哪块地种玉米能高产,哪片山的草药能治咳嗽,都是真本事。”
“我懂。”沈竹礽点点头,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以前江南也这样。懂风水的人不敢明着教徒弟,都躲在山里或村里当‘隐士’——有的在药铺当坐堂先生,有的在私塾教孩子读书,暗地里才把看地脉、辨星宿的学问传下去,就怕被卷进政治里。”
他看向王二婶,眼神里带着认同,“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讲究科学,这是好事,但传统学问也不能丢。就像风水里看地脉走向,和地质勘探看岩层、土壤,本质上都是在‘懂地’,要是能结合起来,选工厂地址时既知地脉稳不稳,又知地质适不适合盖厂房,不是能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可不是嘛!”王二婶眼睛一亮,刚巧铁壶开了,她拎起壶往粗瓷碗里注热水,茶叶在碗里翻了个滚,香气更浓了,“前阵子工程师来勘探,说俺们选的那块地岩层结实,俺当时就跟他们说,那地是‘青龙抱脉’,地脉稳得很——后来工程师测了,还真跟俺说的一样!你看,这就是结合的好处,他们用仪器测,俺们用老法子看,两边对着来,错不了!”
一首盯着墙上《天文图》的沈砚之,这时候忍不住凑近了些。他个子矮,得踮着脚才能看清图上的细节——图上的二十八宿,他跟着祖父学过,可这张图上的北方星宿,比如斗宿、牛宿,标注得比家里的星图详细多了,连星宿对应的地脉范围都用小字写在旁边。
“王二婶,”他指着图上的斗宿,声音里带着好奇,“这张《天文图》是您太爷爷画的吗?俺家里的星图,北方星宿没这么细。”王二婶放下茶壶,走到墙根下,指尖轻轻碰了碰《天文图》的宣纸:“是俺太爷爷画的。他以前在钦天监当差,专管看星象、辨地脉,这张图是他临走时偷偷画的,上面记了二十八宿和地脉的对应关系——你看,角宿主东方的山脉,像咱们村东边的那座山,就是角宿罩着的,山稳,水土也养人;心宿主南方的平原,就像工厂选址的那块地,平坦,地脉也顺;还有你指的斗宿,”
她指向斗宿的位置,“斗宿主北方的水脉,咱们村后的那条河,就是斗宿对应的,所以常年不干旱,也不发大水。”沈砚之听得认真,赶紧从斜挎的布包里掏出个小笔记本——笔记本是祖父给的,封面己经磨破了,里面记满了他平时学的风水、星象知识。他翻开本子,拿出铅笔,一边对照着《天文图》,一边一笔一画地记:“角宿:东方山脉,稳,养水土;心宿:南方平原,坦,地脉顺;斗宿:北方水脉,常流,不旱不涝……”
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院里的蝉鸣、屋里的茶香混在一起,格外安静。“等俺记完了,”沈砚之抬头,眼里闪着光,“就带回江南给俺爹看,还要教给村里的小伙伴——俺爹常说,好学问得传下去,不能断在咱们这代。”
王二婶看着他认真的模样,又看了看沈竹礽,忍不住笑了:“说得好!学问就是这样,你传我,我传他,不管是江南的‘隐士’,还是东北的‘出马仙’,说到底都是在护着这份传承。以后你们要是还想了解这两张图,随时来俺家,俺把俺太爷爷留下的笔记也给你们看。”
沈竹礽端起粗瓷碗,喝了口热茶,茶香里带着暖意。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屋里,落在《天文图》和《风水图》上,淡墨的线条、朱红的圆点,在光里像是活了过来——那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也是砖房里藏着的、最珍贵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