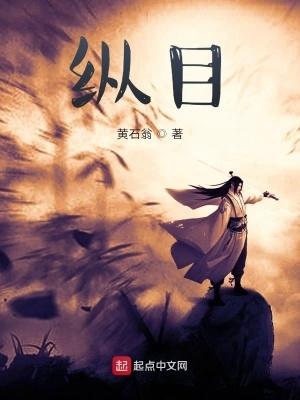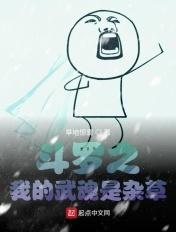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心墟是什么意思 > 第50章 理性主义者的感性瞬间(第1页)
第50章 理性主义者的感性瞬间(第1页)
星空下的概率告白,像一道无形的契约,将陈序与楚月的关系正式锚定在“灵魂伴侣”的维度。没有世俗的鲜花烛光,没有黏腻的甜言蜜语,他们的关系确立,发生在凌晨三点的研究所天台,以宇宙的宏大和概率的渺小作为见证。这本身,就充满了某种极致的、属于他们二人的浪漫。
关系的初期,是陈序情感“考古”生涯中从未体验过的和谐与纯粹。他们仿佛找到了失落己久的思维拼图,沉浸在一种近乎完美的智力共生状态。
他们的约会地点,常常是研究所的办公室、大学的图书馆,或是某个提供白板和高速网络的咖啡馆。约会的内容,是持续不断的思维风暴。他们会就一个哲学悖论争论整个下午,会因为突然灵光一闪的跨学科灵感而兴奋地通过邮件或即时通讯软件激烈讨论到深夜,哪怕彼此只相隔几个街区。
思念,在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楚月会在深夜发来一条信息,没有文字,只有一个简洁的数学方程:
【∫?^∞e^(-x2)dx=√π2】
后面附言:【看到这个高斯积分,想到了你昨天提到的“社会系统的正态分布与长尾效应”。它的优美和普适性,让我感到一种…逻辑上的思念。】
陈序则会回复一个物理学公式:
【E=mc2】
附言:【能量与质量的等价,如同我对你的“共鸣”与“存在感”,本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份“能量”此刻正跨越空间,作用于我。】
他们用薛定谔的猫来比喻关系确定前那种既存在又不确定的叠加状态;用熵增定律来调侃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琐碎与混乱;用宇宙膨胀来隐喻彼此思维疆域在对方影响下的不断拓展。
他们甚至尝试用数学来“建模”他们的爱情。楚月半开玩笑地说:“或许我们的关系,可以看作一个高维流形,在‘智力’、‘信任’、‘共鸣’等多个维度上都存在强烈的吸引子,使得我们的轨迹被牢牢地束缚在一起。”
陈序则认真地补充:“还需要引入一个‘非理性扰动’参数,虽然微小,但或许正是它,使得这个系统避免了陷入完全可预测的平衡态,保持了活力。”
他们都为这个想法笑了起来,认为他们找到了超越俗世柴米油盐的、真正属于“精神贵族”的爱情模式。他们爱上的,仿佛是对方那个高度有序、逻辑自洽、并能与自身产生强烈共振的思维世界。在这种极致的智力交融中,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愉悦和满足,仿佛两个顶尖的舞者,在思想的舞池中跳着无人能及的探戈,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对方的节奏和预期上。
陈序严格地遵守着他的“角色”。他谨慎地维持着思维的同步率,确保自己输出的每一个观点,都能与楚月的认知框架完美契合,或者至少能引发她有益的思考。他像一个最高明的模仿者,不仅模仿她的思维模式,更模仿她对待情感的那种理性化、去情绪化的态度。
他成功地让她相信,他和她是同一类人——超越了低级情感需求,在纯粹理性的国度里相遇相知的同类。
然而,在这片看似完美的理性乐土之下,陈序偶尔会感到一丝极其细微的、难以言喻的异样。
有一次,楚月感冒了,有些低烧。陈序按照常规情侣的模式,带了药和粥去看她。楚月开门时,脸上带着病容,但眼神依旧清明。她接过东西,礼貌地道谢,然后很自然地开始分析病毒的传播模型和自身免疫系统的响应机制,并建议陈序保持距离以避免交叉感染。
她没有流露出丝毫脆弱,也没有对这份关怀表现出特别的感动,仿佛这只是两个合作者之间一次高效的问题处理。
陈序按照“理性伴侣”应有的反应,表示了理解,并配合地讨论了十分钟的免疫学,然后主动告辞。离开楚月的公寓,走在寒冷的夜风里,他忽然想起,如果是苏婉清,或许会默默地给他倒一杯更热的茶;如果是何璐,可能会因为这份关怀而眼眶泛红。
那一刻,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空洞。这种完全剔除了情绪冗余的、极致高效的互动,像一台永不出错的精密仪器在运转,完美,却……没有温度。
但他很快将这点异样压了下去。他告诉自己,这正是他追求的啊!验证“智性恋”命题,不就是要体验这种剥离了世俗情感的、纯粹的精神联结吗?这丝空洞,或许只是他自身尚未完全进化到纯粹理性境界的证明。
他将这点感受,记录在了他的“实验笔记”中,归类为“非典型干扰情绪,需排除”。
他继续沉浸在这场由公式和逻辑编织的梦境里,享受着楚月毫无保留的智力信任与共鸣。
他们都以为,找到了通往伊甸园的密钥。
却不知,这座由纯粹理性构筑的巴别塔,其地基之下,正悄然酝酿着无法用公式计算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