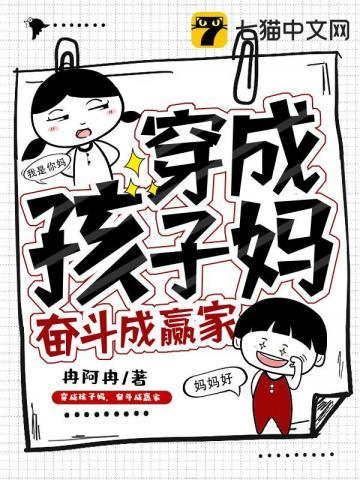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儒商是啥意思 > 第49章 产学循环(第2页)
第49章 产学循环(第2页)
颜路先唱《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表示鲁国愿意用丝帛换齐国的海盐。子琴却唱《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表示齐国担心鲁国会反悔。
颜路立刻改唱《大雅?大明》:“上帝临女,无贰尔心”——表示鲁国愿以宗庙为誓。
子琴这才点头,唱《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表示齐国愿意提供足够的海盐。
“这就是言语的智慧。”孔丘总结道,“不是耍嘴皮子,是用《诗》的道理,让对方明白你的诚意,也让你明白对方的顾虑——邦交如此,与人相处也如此。”
言语科上完课后,孔丘走向文学科。
文科堂讲堂在南侧,案上堆着《诗》《书》《礼》《乐》的竹简,这堂课孔丘要给弟子们讲《礼》的源流。
“你们知道‘丧礼’为什么要‘守灵三日’吗?”他拿起一卷竹简说,“上古时,人死后可能会‘假死’,守灵三日,是为了确认逝者真的离世——这是‘礼’的本源,是对生命的敬畏。”
他又拿出另一卷竹简:“可后来,贵族把‘守灵’变成了炫耀的方式,守灵时要摆上百坛酒,请来乐师奏乐——这就丢了‘礼’的本义,只剩‘奢’的外壳。”
九岁的颜回问:“夫子,那我们整理典籍,就是要找回‘礼’的本源吗?”
“是,也不是。”孔丘摇头,“找回本源,是为了让‘礼’适应现在的时代。比如‘仁俭安魂’套餐,就是把‘守灵三日’简化为‘守灵一日’,却保留了对逝者的敬畏——这就是‘礼融仁行’。”
文学科的弟子们开始抄录典籍,孔丘让他们在每卷竹简后加一段“注”,写下自己对“礼”的理解——他要的不是复刻典籍,是让典籍里的“礼”,能走进庶民的生活。
去年孔学私塾把西侧的一块地买了过来,重新建造了讲堂,成为儒商西技的学区。
礼生技学区的弟子们正在晨练吊嗓。
庶民弟子阿土站在队伍里,跟着老师喊:“哀哉吾母,生我劬劳!”可他刚喊两句,就哭岔了气——他想起母亲采桑的手,心里又酸又疼。
老师李伯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背,“哭!不是嚎!声音从这里出来!”李伯指着自己横膈膜位置,“哭不是装样子,是把心里的话喊出来。你娘对你好,你就喊‘娘啊,儿想你’;若逝者是孤寡老人,你就喊‘老人家,一路走好’——要让丧主觉得,你懂他的苦。”
李伯让弟子们模拟“庶民丧礼”:阿土扮演丧主的儿子,要在灵前哭丧半个时辰。
一开始,阿土还放不开,可想到母亲,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哭声也越来越真——最后,连旁观的弟子都红了眼。
“这就对了。”李伯点头,“礼生的‘礼’,不是看甩袖的角度,也不是熟背祝词模板,而是体谅。你若不懂丧主的苦,再标准的仪程,也是冰冷的。”
礼生技还有“尸体旁伴”的实操课,有儒商曲阜会馆指定新丧户让礼生技弟子参加,有个叫阿桃的女弟子,第一次守灵时,看到逝者的脸,吓得差点跑出去。
可老师告诉她:“逝者是丧主的亲人,你守着他,丧主才能安心——这是你的责任。”
后来,阿桃不仅敢守灵,还会给逝者擦脸、整理寿衣——她总说:“就像给我奶奶整理衣服一样,没什么可怕的。”
棺木技的工坊里,满是木头的香气。
鲁木匠正拿着一块柏木,教弟子们分辨木材:“你们敲敲这块柏木,声音浑厚,是‘活木’,做棺木耐腐;再敲这块杉木,声音清脆,是‘死木’,只能做练习棺。”
弟子阿木拿起一块木头,敲了敲,声音发闷。“鲁师傅,这是什么木?”
“是‘朽木’。”鲁木匠摇头,“若用这种木做棺木,不到半年就会烂——丧主花了钱,逝者却不安宁,这是坏良心的事。”
棺木技的实操课是“当日打一口练习棺”,阿木第一次做榫卯,怎么也拼不上,急得满头汗。
鲁木匠走过来,手把手教他:“榫卯要对齐,就像人要守规矩——差一分,就合不上;差一寸,就会散。”
后来,阿木做的棺木通过了“抗压测试”:三个成年人踩在上面,棺木纹丝不动。
他拿着自己做的棺木,眼泪都流下来——他想,以后要给家乡的人做最好的棺木,让他们能体面地离开。
棺木科还有“防潮密封”的课。鲁木匠教弟子们用动物胶加漆树汁,调制成密封剂:“棺内湿度要不能太高,这样逝者遗体才不会腐坏,丧主也不会闻到臭味——这是我们的本分。”
织染技的染坊里,飘着草木灰的味道。
老师桑姑正拿着一把茜草,教弟子们染色:“茜草泡在草木灰水里,三天就能出红色——这是‘斩衰’的颜色,是子女为父母穿的丧服色,要染得深,才显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