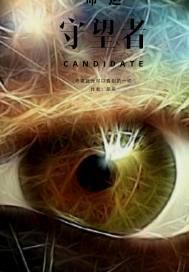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文始道是什么门派 > 第9章 立誓守本心(第1页)
第9章 立誓守本心(第1页)
尹喜二十二岁这年的暮春,函谷关的风带着暖意,吹得关楼的旗帜舒展如翼。关下的黄河刚过了汛期,水流平缓,倒映着两岸新绿的柳枝,像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这日清晨,守关的士兵忽然来报,说洛邑来了位使者,带着周天子的旨意,正候在关下。
使者乘着一辆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帘绣着日月星辰的纹样,车夫穿着朱红色的袍服,腰间挂着青铜剑,一看便知是来自周天子的仪仗。他走进尹府时,手里捧着一卷明黄色的丝绸,那是周天子的诏书,卷轴末端缀着的玉坠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尹公子,”使者站在庭院中央,声音洪亮如钟,“周天子听闻公子观星之术冠绝天下,特下旨意,召您入宫担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辅佐君王洞察天意。”
太史令,这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掌管天文历法,修订律历,记录灾异,不仅能接近权力中心,更能让自己的星象之学得以施展,名垂青史。尹府的仆役们都屏住了呼吸,眼神里满是羡慕——谁都知道,这是天大的荣耀,是尹家祖坟冒了青烟。
尹虔接过诏书,手指微微颤抖。他一辈子守在函谷关,最大的心愿便是尹家能出个栋梁之材,如今儿子能被周天子看中,怎能不让他激动?“喜儿,还不快谢恩?”他转身看向尹喜,眼中的喜悦几乎要溢出来,“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去洛邑吧,你的本事,该在更大的舞台施展。”
尹喜却站在原地没动。他望着使者带来的那卷诏书,明黄色的丝绸在阳光下有些刺眼,像极了洛邑宫殿的琉璃瓦,华美却带着疏离。他的目光掠过庭院里的老槐树,掠过墙角那株方士留下的启明草,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闷的。
他想起三年前去过一次洛邑。那时他跟着尹虔去述职,见了太多朝堂的纷争:大夫们为了一点封地争得面红耳赤,卿士们为了权力相互倾轧,连太史令府里的官员,都在为了谁能靠近天子而费尽心机。那里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看不见的尘埃,让人喘不过气。
他更想起自己夜观星象时,看到的洛邑上空的星象。太微垣对应着朝廷,本应像《夏小正》里唱的“太微五帝坐中央,内坐九卿外藩臣”,井然有序。可洛邑的太微垣,星象总是混乱不堪:辅星忽明忽暗,像朝臣摇摆不定的心;执法星光芒黯淡,像律法被权力践踏;甚至连五帝座旁,都总有几颗客星闪烁,像那些觊觎权位的野心家。那片星空,乱得像一团理不清的麻,远不如函谷关的星空清澈。
“公子?”使者见他迟迟不应,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容我三思。”尹喜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
那夜,尹喜没有点灯。他独自登上函谷关的城楼,关楼的风比平日里更凉些,吹得他的衣袍猎猎作响。他望着洛邑的方向,那里的夜空被一层淡淡的云气笼罩,连最亮的天狼星都显得模糊,仿佛连星辰都被那座繁华的都城染上了尘嚣。
他想起自己十二岁时,在书房的帛布上写下的“澄怀”二字。那时的笔迹还带着稚气,却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像是在刻下一个永不更改的誓言。他记得自己当时想,要让心像函谷关的星空一样清澈,不被世俗的纷争扰乱。
他又想起方士说的“后天之行决定命运”。方士说,星象是先天的种子,而后天的选择才是土壤。洛邑的太史令之位,像一颗的种子,落在权力的土壤里,或许能结出富贵的果实,可那样的土壤,会不会让他忘记“澄怀”的初心?会不会让他观星时,眼里看到的不再是天地的真相,而是权力的影子?
他低头看向胸口的玉牌,那枚刻着北斗的玉牌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像一颗缩小的星辰。他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帮农夫们预测旱灾,看着他们用储水浇活的庄稼,脸上露出的笑容;想起二十岁那年,教士兵们辨星识方位,看着他们在荒漠里找到归途时的庆幸;想起这些年,函谷关的星空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见证了他与这片土地的联结。
这里的星空,能让他看清角宿升起时春气的萌动,能让他听懂奎宿西沉时秋收的喜悦,能让他感受到每一颗星与百姓生计的关联。而洛邑的星空,恐怕只能让他看到权力的更迭,听到欲望的低语。
“原来我早就有答案了。”尹喜喃喃自语,夜风掀起他的发丝,露出额间那道淡淡的星纹,在月光下清晰了许多。
第二日清晨,尹喜来到使者的住处。使者正在收拾行装,见他进来,便笑着说:“公子想通了?也是,这般前程,可不是谁都能遇到的。”
尹喜却摇了摇头,对着使者深深一揖:“多谢大王厚爱,只是我志在观星,不在朝堂。”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函谷关的星空最清,能让我看清天地的真相,若入洛邑,恐被尘嚣扰了本心,反倒辜负了大王的信任。”
使者愣住了,手里的玉佩“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公子可知自己在说什么?”他捡起玉佩,语气里带着难以置信,“多少人为了一个接近天子的机会,费尽毕生心血。你年纪轻轻,怎能甘居关外?入了朝,才能用星象辅佐君王,安定天下啊。”
“安定天下,未必非要在朝堂。”尹喜道,声音平静却有力,“我守函谷关,观星象以预警灾祸,让农夫们不失农时,让士兵们不迷方向,护一方百姓平安,亦是安定天下的一种方式。若入朝堂,每日周旋于权谋纷争,恐为权力所惑,观星时掺杂私心,误判了星象,那才是真的误了大事。”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砸在使者心上。使者张了张嘴,想再说些什么,却见尹喜眼神坦荡,没有丝毫犹豫,便知道再多说也无用。“罢了,”使者叹了口气,“公子既有此志,我也不强求,只是回去后,需如实向大王禀报。”
尹喜拒绝周天子征召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函谷关。有人说他傻,放着太史令的大好前程不要,偏要守在这关外喝风沙;也有人说他清高,仗着自己懂星象,就不屑与朝臣同流合污;连尹虔起初也有些不解,首到尹喜把自己的想法细细说了一遍,他才沉默着点了点头:“你想守的,不只是这关隘,更是自己的心。爹懂了。”
那晚,月色格外明亮,像一层银霜覆盖了函谷关。尹喜独自来到关楼脚下,那里有一块青石板,是他年少时亲手刻的北斗星轨。岁月的打磨让石板变得光滑,可那些刻痕依旧清晰,尤其是斗柄末端,比寻常星轨偏出三寸——那是他特意刻的,提醒自己凡事留三分余地,更要守住三分本心。
月光洒在石板上,斗柄偏出的三寸在月色中格外清晰,像一道沉默的警示。尹喜整理了一下衣袍,对着星空缓缓跪下。他的膝盖落在青石板上,冰凉的触感从膝盖传来,却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
“我尹喜在此立誓,”他抬起头,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像钟磬般清澈,“此生唯观星求道,不问权谋,不慕富贵,不因尘俗纷扰而改澄怀之志。以我之眼,察天地玄机;以我之心,护苍生安宁。若违此誓,愿受星辰唾弃,天地不容。”
话音落下,夜风忽然掠过关楼,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无数星辰在为他作证。胸口的玉牌微微发烫,那股暖意顺着血脉流遍全身,与额间的星纹相互呼应,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注入他的体内,坚定而温暖。
他缓缓站起身,望着漫天繁星。北斗七星高悬北方,角宿在东方闪烁,井宿在南方明亮,奎宿在西方沉静,每一颗星都像在对他点头,认可他的誓言。他知道,这条路或许孤独,或许清贫,或许永远不会像太史令那样名满天下,却能让他守住本心,不辜负那些日夜陪伴他的星辰,不辜负自己对“道”的追寻。
关下的黄河,在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像一条银色的带子,静静流淌。尹喜站在青石板旁,望着远方的星空,忽然觉得,自己与这函谷关、与这星空、与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早己融为一体。就像北斗星永远守着北方,他也将永远守着这里,守着自己的初心,首到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