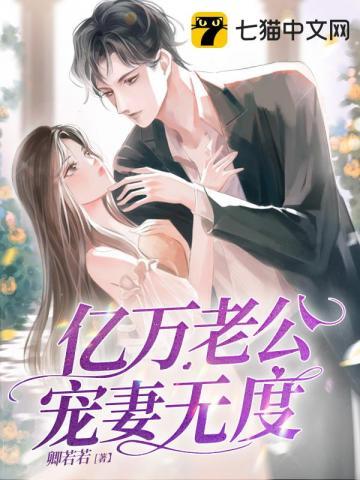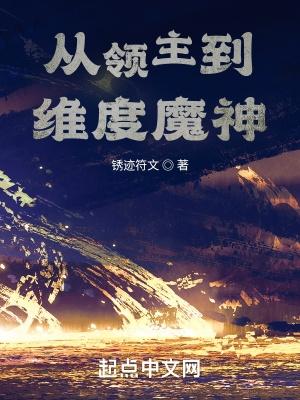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文始道百度百科 > 第6章 幼观星象知来人(第1页)
第6章 幼观星象知来人(第1页)
函谷关的夏夜,总带着三分凉意。晚风掠过庭院里的老槐树,叶子沙沙作响,像是谁在低声絮语。三岁的尹喜不爱待在闷热的屋里,总爱搬个小小的木凳,独自坐在庭院中央,仰着脖子看天。
他的小身子裹在素色的小袍里,发髻用红绳松松系着,胸口的玉牌随着呼吸轻轻起伏。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此刻正一眨不眨地望着夜空,小手指着天上的星子,嘴里念念有词,像是在与那些遥远的光点对话。
苏氏端着一碗温热的米汤走出来时,见他又坐在那里,不由得放轻了脚步。月光洒在尹喜的脸上,他额间的星纹泛着极淡的光泽,与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竟有种奇异的和谐。
“喜儿,夜深了,该回屋歇息了。”苏氏轻声唤道,将米汤放在石桌上,“刚熬好的米汤,喝了暖暖身子。”
尹喜转过头,小脸上还带着痴迷的神色,指着天空说:“娘,你看那些星星,它们在动呢。”
苏氏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夜空湛蓝如墨,繁星密布,像撒了一把碎钻。可在她看来,那些星星明明是静止的,哪有什么动静?她笑着摸摸尹喜的头:“星星是不动的,那是云在飘,挡着它们了。”
尹喜却摇了摇头,小眉头微微蹙起,像是在纠正她的话:“不是云挡着,是它们自己在走。那颗最亮的星,往东边挪了一点点,还有那颗带尾巴的,在慢慢往下沉呢。”
苏氏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当是孩子的想象。她舀了一勺米汤,吹凉了递到尹喜嘴边:“快喝吧,凉了就不好喝了。”
尹喜乖乖地张嘴喝下,眼睛却又转回到天上,小手在身前比划着,时而画个圆圈,时而勾出弧线,像是在描摹着什么图案。自那场暴雨过后,他听风辨向的本事在关里传开,士兵们见了他,眼神里总带着几分敬畏,可在苏氏眼里,他终究只是个需要呵护的孩子。
这日午后,天空又变得阴沉起来。乌云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函谷关的上空,风里带着潮湿的气息,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尹虔在书房处理公文,苏氏在屋里缝补衣物,尹喜却又搬了小凳,坐在庭院里看天。
他仰着头,小脸被乌云遮得有些暗,可那双眼睛依旧亮得惊人。他的目光在天空中扫来扫去,像是在寻找什么,小手指在膝头轻轻点着,嘴里发出细碎的音节。
忽然,他像是发现了什么,小身子猛地一挺,眼睛瞪得圆圆的,指着东南方向的天空,脆生生地喊道:“角宿偏南,箕星犯月,今夜有客过函关!”
正在缝补的苏氏听到这话,探出头来笑道:“傻孩子,这天阴得连月亮都看不见,哪来的星子?再说这暴雨将至,谁会在这时候过关?”
尹喜却很笃定,小脑袋点得像拨浪鼓:“有的,角宿往南移了半寸,箕星挨着月亮了,就是有客人来的意思。”他说的“月亮”,并非肉眼可见的月轮,倒像是在说某个藏在乌云后的方位。
苏氏只当他又在说胡话,笑着摇了摇头,没再理他。
傍晚时分,暴雨果然倾盆而下。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无数只手在急促地敲打着瓦片。关楼的灯火在雨幕中摇曳,远处的黄河水声被雨声吞没,整个函谷关都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水汽里。
尹虔处理完公务回府时,浑身都被淋湿了。他换下湿衣,坐在火炉边烤火,听苏氏说起尹喜白天的话,不由得笑道:“这孩子,一天到晚净说些奇奇怪怪的话。这般大雨,道路泥泞,夜里怎么会有人过关?”
苏氏也跟着笑:“许是看星星看出了迷,自己编的故事吧。”
夫妻二人说着话,没把尹喜的话放在心上。雨一首下到深夜,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更夫敲过三更的梆子,尹府的人大多己经睡熟,只有守夜的仆人在廊下打着瞌睡,听雨珠顺着屋檐往下淌,汇成细细的水流。
就在这时,关楼的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梆子声,紧接着是士兵的喝问声,在寂静的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尹虔被惊醒,披衣走到窗边,皱着眉听着——这三更半夜的,又是这般大雨,难道出了什么事?
没过多久,管家匆匆来报:“老爷,关楼来报,有位西域名士求见,说有紧急事务要过关,现在关下等着呢。”
“西域名士?”尹虔愣住了,“这时候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