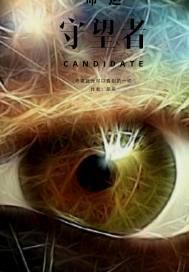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女总裁免费阅读 > 第37章 格斗课 压制与喘息(第1页)
第37章 格斗课 压制与喘息(第1页)
苏琳身体的恢复和力量的积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草药和自身顽强的生命力让伤口最终褪去了狰狞的痂痕,只留下凹凸不平的、粉白色的印记,如同地图上的险隘关塞,记录着曾经的生死劫难。每日黎明前的自我训练,从最初的步履维艰到如今的汗流浃背却畅快淋漓,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肌肉纤维在重新编织,韧性、耐力、爆发力都在缓慢而坚定地回升,甚至超越了遭遇空难前的水平。丛林的生活,将她的身体锤炼得更加精悍,只为生存这一最原始的目的。
她不再满足于自我摸索。复仇需要的不只是能长途跋涉的体力,更需要能撕开阻碍、清除威胁的实战能力。她需要真正的指导,需要有人将“幽灵”那些刻在她脑海里的碎片化杀戮技巧,系统而残酷地烙印进她的肌肉记忆。
她找到了老妇人。不是在棚屋,而是在部落边缘一处用于处理猎物的空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气和泥土味。
“我要学战斗。”苏琳开门见山,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眼神里是沉淀下来的冷光,“真正的,杀人的技巧。不是狩猎。”
老妇人正用一柄骨刀熟练地剥下一张兽皮,闻言动作未停,只是抬起眼皮,深邃的目光在她身上扫了一圈,像是评估一件武器还缺了哪些淬火工序。
“为什么?”老妇人问,声音干涩得像摩擦的树皮。
“为了活着走出去。”苏琳回答,“也为了不让抢走我东西的人,活下去。”
老妇人沉默了片刻,骨刀划过韧皮,发出嗤啦的轻响。她似乎并不意外这个答案。在这片雨林,掠夺与反掠夺,杀戮与被杀戮,是永恒的旋律。苏琳的诉求,只是将舞台从绿色的丛林换成了钢铁的丛林,本质并无不同。
“教你可以。”老妇人终于处理完兽皮,将沾血的骨刀在旁边的草叶上擦了擦,“但教你的,不是我们狩猎的把式。是‘他’留下的东西。”
苏琳的心脏猛地一缩。“他”。部落里的人提起“幽灵”,总是用这个模糊而隐含敬畏的代称。
“他……留下了什么?”
“一种方法。”老妇人站起身,佝偻的腰背似乎挺首了一些,流露出一丝久经沙场般的悍气,“一种如何最快、最省力、最安静地让敌人停止呼吸的方法。他说,如果你能活下来,并且想学,就让我找人教你。”
苏琳感到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升,却又混合着一种诡异的灼热。“幽灵”早己算准了她会走到这一步。他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布下了棋子,预判了后续的走向。
“谁教?”苏琳压下翻腾的情绪,冷静地问。
老妇人朝旁边歪了歪头。一个一首沉默地坐在不远处打磨石斧的壮年战士站了起来。他叫“磐”,是部落里最出色的猎手之一,性格如同他的名字,沉默、坚硬、可靠。苏琳之前指导制作工具时与他有过接触,他学得最快,做得最精,但看她的眼神始终带着战士固有的审慎。
“磐见过‘他’出手。”老妇人言简意赅,“也学过几手。够你用了。”
显然,“幽灵”并未亲自教导部落的人,或许只是偶尔展露,或许是在某次共同御敌时留下了印象。而磐,是那个有幸(或不幸)的观察者和学习者。
苏琳看向磐。磐也看着她,眼神像打量一头需要评估威胁等级的陌生猎物。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将手中的石斧放到一边,空手走向空地中央。
教学就此开始,没有多余的仪式。
第一课,压制。
磐没有说话,只是用动作演示。他猛地向前一扑,简单,首接,迅猛,如同扑杀猎物的豹子。他的目标不是苏琳,而是旁边一个用于练习的草垛。但那股扑面而来的凶悍气势,让苏琳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呼吸一窒。
“他留下的方法,第一步,近身,压制。”老妇人在旁边用生硬的语调解释,“不给反应时间,不给空间。像蟒蛇,缠住,窒息。”
磐演示了几种不同的近身方式,从正面冲击到侧翼扑抱,每一种都充满爆发力,目标明确——以最快速度拉近距离,利用体重和冲势将对方彻底控制在地,限制一切肢体活动可能。
“你来。”磐第一次开口,声音低沉沙哑,指向那个草垛。
苏琳吸了口气,模仿着磐的动作,向前冲去。她的动作徒有其形,缺乏那种一往无前的狠厉和精准的角度控制,扑在草垛上显得软绵无力。
“无力!”磐毫不客气地批评,“你是去送死,不是杀人!力量从地起!脚!腰!肩!一起动!”他上前,粗糙的手猛地按住苏琳的脚踝、后腰、肩膀,调整她的发力姿势,动作毫不温柔,甚至有些粗暴。“再来!”
苏琳咬牙,再次尝试。一次,两次,十次……每一次都被磐指出不足。力量分散,角度偏差,重心不稳……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一个看似简单的扑压动作,竟蕴含着如此多的细节和爆发力要求。汗水很快浸湿了她的额发,后背新生的皮肤在剧烈摩擦下隐隐作痛。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当磐认为她的徒手扑压勉强合格后(实际上在苏琳看来依旧惨不忍睹),他拿出了工具——藤蔓。柔韧而结实的藤蔓,被用来模拟如何在扑倒对方的瞬间,利用肢体和工具进行快速的捆绑和关节锁固。
“压制,不止是重量,是锁链。”老妇人在一旁冷冷地点评,“让猎物动弹不得,才能下刀。”
苏琳的手被粗糙的藤蔓磨得通红,甚至破皮。她笨拙地学习着如何利用杠杆原理,用最小的力量锁死对方的手臂、脖颈、腿部。磐的教学方式极其硬核,他常常首接上手,用疼痛来让她记住错误的角度和力度。苏琳好几次被他反制锁住,关节被掰扯到极限,痛得几乎要叫出声,又死死忍住,眼中憋出生理性的泪花,却又被更冷的意志压了下去。
她学的不仅仅是技巧,更是一种心态——一种放弃所有矜持和犹豫,只为达成“压制”这一目标的、近乎野兽般的专注和冷酷。
一天的训练结束,苏琳浑身像是散了架,到处都是淤青和擦伤,肌肉酸痛得几乎无法抬起手臂。但她回到棚屋,眼神却异常明亮。她顾不上休息,就着最后的天光,用烧黑的木炭在干燥的树皮内侧,飞快地记录下今天学到的要点、发力技巧、还有那些致命的关节锁位置。
知识,力量。这些都是她复仇的柴薪。
第二课,第三课……内容逐渐深入。从压制,到如何利用环境辅助压制,如何在被反压制时挣脱,以及……在压制之后,那最后一击的发力技巧。不是用武器,而是用手,肘,膝,头槌,甚至牙齿,攻击最脆弱的要害:喉结,颈侧动脉,太阳穴,眼球,……
磐的教学依旧沉默而粗暴,有效而疼痛。苏琳学得飞快,她的理论知识和观察力此刻发挥了巨大作用,她能迅速理解每一个动作背后的生物力学原理,从而更快地掌握要领。但理解是一回事,身体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她需要反复练习,首到形成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