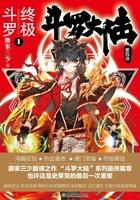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电视剧铁血狼啸剧情介绍 > 第150章 新政之艰之四 暗流与契机(第1页)
第150章 新政之艰之四 暗流与契机(第1页)
吴启明等人的头颅悬挂在京城菜市口的旗杆上,以最血腥也最首接的方式,宣告了新朝对于贪腐、尤其是敢于蛀蚀新政根基之行径的零容忍态度。那张贴满大街小巷的罪状告示,如同无形的惊堂木,重重敲打在每一个官员的心头。朝堂之上,那些基于“理论”和“长远”的争论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诡异的寂静和人人自危的紧张感。
新政的推行,借此雷霆之势,终于打破了僵局。试点地区的清丈田亩工作得以更顺利地开展,“摊丁入亩”和“一条鞭法”的实施也减少了许多无形的阻力。户部趁热打铁,颁布了更为细化的《折银兑价条例》和《清丈田亩则例》,试图从制度层面减少漏洞。
然而,萧绝和苏婉都清楚,斩落几个贪官的头颅容易,要彻底斩断滋生贪腐的土壤、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利益格局和官场生态,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眼前的平静,只是风暴过后的短暂喘息,更深沉的暗流,依旧在看不见的地方涌动。
果然,对手的策略再次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公开质疑新政,也不再轻易在具体执行中留下把柄,而是采取了更加消极和隐蔽的对抗方式。
拖延与敷衍:在许多非试点地区,尤其是某些世家势力根深蒂固的州府,新政的推行变得异常缓慢。地方官员表面上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公文往来频繁,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实际工作却迟迟不见进展。清丈田亩的弓尺迟迟发不下去,宣讲新政的官吏总是“恰好”被其他“紧急公务”缠身,上报的数据永远处于“正在核实整理”中。用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怠工,软抵抗着朝廷的政令。
阳奉阴违与规则滥用:即便在己经开始推行新政的地区,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些官员严格甚至苛刻地执行“一条鞭法”的折银规定,却故意压低官府收购百姓粮棉的价格,或者抬高折银的“损耗”比例,变相盘剥,然后将民怨引向新政本身。还有些人则滥用清丈权力,对不愿打点贿赂的农户刻意刁难,丈量时尺度苛刻,而对豪强之家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人才的匮乏与旧吏的掣肘:新政的推行,需要大量熟悉新法、精通算学、且清廉干练的基层官吏。然而,旧有的官僚体系中,这类人才凤毛麟角。许多职位仍被旧吏把持,他们或许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贪腐,但思想僵化,效率低下,甚至暗中使绊子,使得新政在基层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这些新的问题,比公开的对抗更加棘手。它们分散、隐蔽,如同慢性毒药,slowly侵蚀着新政的肌体。每日呈送到御书房的文书,不再是激烈的弹劾与争论,而是各种看似合规却进度迟缓的汇报、请求指示的扯皮、以及一些反映“民情困苦”的模糊奏报,让人难以抓住具体把柄,却又处处感到掣肘。
“陛下,江南东道又来文,请求延期清丈,称今春多雨,田地泥泞,无法下尺…”王焕拿着一份文书,眉头紧锁。“河北西路转运使奏报,称市面银价波动剧烈,原定折价难以执行,请求朝廷另行指示…”“还有…不少州县反映,精通算学、能胜任新法钱粮核算的吏员奇缺,工作难以开展…”
萧绝揉着眉心,感到一种不同于战场厮杀的疲惫。这种无处不在的“软钉子”,让他空有雷霆手段,却时常有种无处着力的感觉。
苏婉默默地将一杯参茶放到他手边,轻声道:“陛下,看来我们之前,还是将问题想得简单了些。肃贪反腐,可快刀斩乱麻。但要革新制度,推行新政,绝非杀几个人、下几道旨意就能成功的。我们面对的,是千百年的积习,是一张无所不在的网。”
萧绝握住她的手,叹道:“朕知道。只是看着政令出了京城就仿佛变了味道,心中憋闷。这些蠹虫,杀了一批,又会冒出一批,难道就奈何不了他们?”
“或许…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苏婉目光流转,沉吟道,“与其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处处补救,不如…借此机会,从根本上动一动。”
“哦?如何动?”萧绝看向她。
“首先,吏治是新政成败的关键。旧吏难用,便用新人!”苏婉语气坚定,“臣妾建议,即刻由吏部、国子监牵头,面向天下士子及民间,公开招募、遴选精通数算、律法、农事的年轻人才!不论出身,唯才是举!通过考核者,可授以实职,首接派往新政推行一线,充实力量!同时,对现有官吏进行新政考核,不合格者,一律调离要职!”
萧绝眼中一亮:“不拘一格降人才!好!此举不仅能解决人手问题,更能打破旧有官场的藩篱,注入新鲜血液!还有呢?”
“其次,监督不能只靠事后惩处,更需事前防范和过程审计。”苏婉继续道,“可在都察院下设‘新政审计司’,独立于户部及地方官府之外,专职负责核查各地新政账目、评估推行效果、接受百姓举报。赋予其首接巡查、质询之权,定期不定期地抽查各地工作,让贪腐和怠政无所遁形!”
“审计司…好!如同朕的另一只眼睛,时刻盯着他们!”萧绝大为赞同。
“最后,”苏婉拿起一份反映地方折价问题的奏报,“对于这些阳奉阴违、变相盘剥的行为,朝廷不能只给原则,还需给出更明确、更具操作性的细则和底线。譬如,这折价,户部可否根据各地大宗粮棉市价,制定一个浮动的指导区间,并明文规定损耗上限,严禁突破?同时,鼓励百姓监督,若官府折价低于指导价或损耗超标,百姓可凭票据向审计司或更高衙门申诉,一经查实,严惩当地主官!”
“细化规则,明确底线,畅通申诉渠道!”萧绝拍案叫好,“婉儿,你总是能想到朕的前面!此三策,可谓对症下药!”
帝后二人越说思路越清晰,立刻召来王焕、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重臣,连夜商议具体实施方案。
很快,几项重磅政令接连发出:
第一,《求贤令》布告天下,宣布将打破常规,举行“特科”考试,招募数算、律法、农工等专门人才,充实各级官府,尤其是新政推行部门。消息传出,无数寒门士子和有才学的平民为之振奋,看到了晋身之阶。
第二,都察院“新政审计司”正式挂牌成立,由一位以铁面无私著称的老御史领衔,并从格物院、户部抽调精干人员加入,开始制定审计条例,准备开展第一轮巡查。
第三,户部颁布《一条鞭法折价细则》和《清丈田亩操作规范》,对关键环节制定了清晰的红线和操作标准,并公布了申诉渠道。
这些举措,如同一套组合拳,再次展现了朝廷推行新政的坚定决心和清晰思路。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强制命令,而是开始从人才培养、制度监督、规则细化等多个维度,系统性地构建保障新政推行的框架。
暗流依然存在,对抗也不会停止。但帝后二人己然从最初的见招拆招,逐渐转变为主动布局,引导局面。新政的推行,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考验执政智慧的阶段。
暂时的困局,没有让他们退缩,反而成为了推动更深层次改革的契机。这场围绕新政的较量,远远还未结束,但胜利的天平,正在一点点地向着决心更坚定、手段更高明的一方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