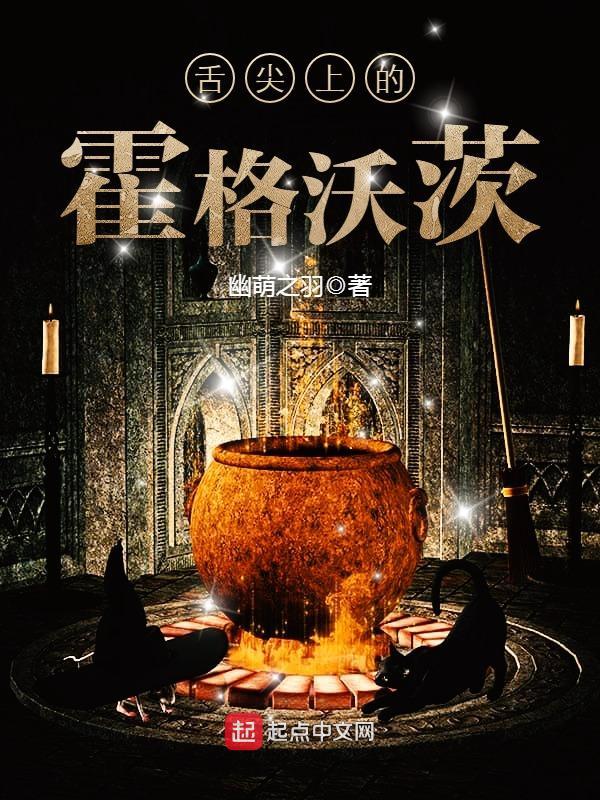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偏执太子恃宠而骄 > 第93章(第2页)
第93章(第2页)
“你拿王家当挡箭牌?”
“枪打出头鸟。”严燊笑得像头嗜血的狼,“王家既贪又蠢,正好替我们试试裴既琛的刀锋利不利。”
裴既白忽然拽住他衣领拉得更近,两人几乎贴在了一起:“然后呢?”
“然后?”严燊抵着他额头低笑,“等他来收拾残局时,会发现所有的‘肥肉’早就被啃得只剩骨头了。”
“你可真是可怕。”
严燊抓住裴既白的手腕按在心跳处:“再等一个月,够我吞下整个金海了,到时候我给你亲手造一个固若金汤的——囚笼。”
——
阿金整理着医务柜里的纱布,动作却比平时慢了许多。
酒精瓶在他手里转了三圈,棉签数了又数,眉头不自觉地拧成结。
“这都第五天了……萧晨那小子真病得这么重?”他忍不住嘀咕出声,指尖无意识地抠着标签边缘。
作为队长,他清楚每个队员的状况——可萧晨这次请假的理由实在蹊跷。
电话永远转接语音信箱,消息回复总是隔了好几个小时,只有简短的“不舒服”三个字。
阿金想起萧晨那苍白的脸和总是怯生生的眼神,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怎么了?今天心情不好?”
清泉般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
沈砚秋不知何时走近,将一瓶冰镇橘子汽水贴在他脸颊。
玻璃瓶沁出的水珠顺着阿金下颌线滑落,激得他猛地回神。
“沈医生!”阿金瞬间站得笔直,方才的愁云惨雾一扫而空,眼睛亮得像撒了星星,“没、没有不开心!”
沈砚秋轻轻笑出声,金丝眼镜后的眸光温柔流转:“不对,你总是藏不住事情,刚刚的不开心都写脸上了。”
阿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耳根唰地红了:“也没什么,就是最近在想一个手下的事情。”
沈砚秋问:“什么事情?”
“就是……在担心一个队员。”他拧开汽水灌了一大口,冰凉的气泡刺得眼眶发酸,“叫萧晨,是我们队里年纪最小的那个。”
“萧晨?是那个喂流浪猫的孩子吗?”沈砚秋倚着药柜微微侧头,“上次看见他蹲在花坛边,用手帕给小三花垫着喝牛奶。”
沈砚秋的白大褂袖口滑落一截,露出白皙的腕间仿佛都散发着淡淡的栀子香气。
阿金看得有些发怔,好一会儿才接话:“对……就是他。明明胆子小得连枪都握不稳,却敢徒手接白刃。”
“温柔的人往往比看起来坚强。”沈砚秋忽然伸手,轻轻拍了拍阿金肩上的灰尘,“他怎么了?”
这个不经意的触碰让阿金浑身一僵,汽水瓶在掌心被他捏得发出细微响声。
他几乎是屏着呼吸回答:“请假五天了,说是生病……但前一天还看见他负重跑完全程。”
夕阳从百叶窗缝隙漏进来,把沈砚秋的睫毛染成暖金色。
阿金看见他喉结轻轻滚动,仿佛咽下了什么未尽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