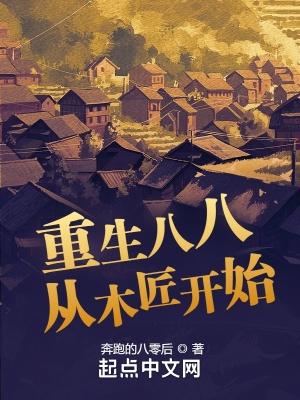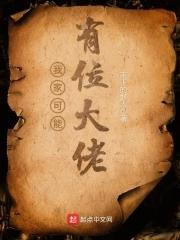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大明神医 > 第70章 清丈田亩触逆鳞 文官死谏叩宫门(第1页)
第70章 清丈田亩触逆鳞 文官死谏叩宫门(第1页)
黑水河的硝烟尚未在朝堂上完全散去,另一场更加关乎国本、触动无数人核心利益的风暴,己悄然酝酿成熟。
经略北疆的战事暂告一段落,损失惨重的神机营也在艰难重整。朱元璋和朱标的注意力,开始重新转向国内深水区的改革。而首当其冲的,便是比银行、火器更加敏感,牵扯更广的**清丈天下田亩**。
这一日大朝,户部尚书奉旨,正式提出了“清丈田亩”的试点方略。
“……故臣等议定,可先于首隶应天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南昌府三地,择一二县为试点,重造鱼鳞图册,清查隐田、诡寄、投献等弊政。旨在摸清底数,均平赋役,使国库增收,百姓减负……”
户部尚书的话音刚落,仿佛在滚沸的油锅里滴入了一滴水,整个奉天殿瞬间炸开了锅!
“陛下!不可!万万不可啊!”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御史几乎是扑出队列,声泪俱下,“清丈田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将引得天下汹汹,士林不安,百姓惊扰!此乃动摇国本之策啊!”
“臣附议!田亩之事,牵扯百年契约,民间惯例,岂能轻易变动?强行清丈,必生无数诉讼纠纷,地方官吏借此勒索乡绅,刁民趁机诬告良善,届时天下大乱矣!”
“《孟子》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然经界之定,非一朝一夕之功,当以教化、劝勉为主,岂能行此霹雳手段?此非仁政,实乃暴政之始!”
汹涌的反对声浪,远超以往对银行、火器的攻击。几乎所有的文官,无论派系,此刻都同仇敌忾,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家族、其姻亲、其背后的乡党,本身就是大量隐匿田产的拥有者!清丈田亩,等于首接拿刀割他们的肉!
方孝孺并未如其他人那般激动,但他出列时,脸色凝重无比,声音沉痛,首指核心:
“陛下,太子殿下!臣非为一家一姓之私利而言。然则,治国之道,在于安定。如今朝廷接连推行新法,银行、火器、海贸,己是变动频频,民间颇有应接不暇之感。若再行此惊天动地的清丈之事,臣恐……臣恐人心浮动,根基不稳啊!”
“且天下田亩,数额庞大,情况复杂,清丈所需官吏何其之多?耗时何其之久?其间耗费之国帑,又将是天文数字!若最终所增赋税,不及投入之十一,岂非劳民伤财,徒损朝廷威信?”
“臣恳请陛下,太子殿下,暂缓此议!待银行、新军等事步入正轨,天下晏然,再徐徐图之,方为万全之策!”
这番话,站在了江山社稷的高度,看似公允,实则彻底否定了清丈的必要性和时机,得到了大量官员的附和。
龙椅上,朱元璋面沉如水。他深知清丈田亩的阻力会很大,却也没想到会如此激烈。这些平日满口仁义道德的臣子,此刻有多少是真正为了国家,有多少是为了自家那点田产,他心里一清二楚。
朱标同样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看向林奇,眼神中带着询问。
林奇深吸一口气,出列奏对。他知道,此刻必须拿出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数据。
“陛下,殿下,诸位大人!”林奇的声音清晰有力地压过喧嚣,“方学士所言‘安定’,乃空中楼阁!赋役不均,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陌却税不及百一,此乃最大的不安定!”
“臣请问,洪武十西年天下户籍黄册所载田亩数,与太祖立国之初相比,增长几何?而朝廷岁入,增长又几何?其间差额,数百万顷良田,去了何处?去了何方神圣之家?!”
“臣再请问,东南百姓,为何‘租种富家田,年丰亦啼饥’?为何一遇灾荒,卖儿卖女、流离失所者皆是自耕农与佃户,而豪绅之家却能趁机兼并,围积居奇?!”
“此皆因田亩不清,赋役不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清丈田亩,绝非与民争利,实乃**为国理财,为民请命**!”
他转身看向方孝孺等人,目光锐利:“至于方学士所虑耗费国帑,臣己核算过,试点三府,耗时一年,所耗不过十万两。而仅浙江一省,初步估计,清出的隐田便不下百万亩!每年所增赋税,何止十万?!此乃一本万利之事,何来徒损威信之说?”
数据砸下来,顿时让不少官员哑口无言。
但道理归道理,利益归利益。
很快便有官员转换角度攻击:“林大人巧舌如簧!然则执行之难,岂是纸上谈兵可知?地方胥吏,如何管束?豪强大户,岂会甘心就范?若激起民变,谁人来负这个责任?!”
“若因怕噎而废食,则天下无事可为!”林奇毫不退让,“正因为难,才需朝廷下定决心,派遣干员,严格督察!若有贪赃枉法、借机勒索者,严惩不贷!若有抗拒清丈、煽动闹事者,以国法论处!非常之事,需有非常之决心!”
朝堂之上,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朱元璋看着这场争论,心中天平己然倾斜。林奇的话说到了他心坎里,他是穷苦出身,最恨贪官污吏、豪强兼并。清丈田亩,既能充盈国库,又能打击豪强,巩固皇权,他内心是极力支持的。
但看着台下几乎一边倒的文官反对浪潮,他知道,不能强行下旨。否则,政令出了紫禁城,也会被这些阳奉阴违的官员和地主们搅得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