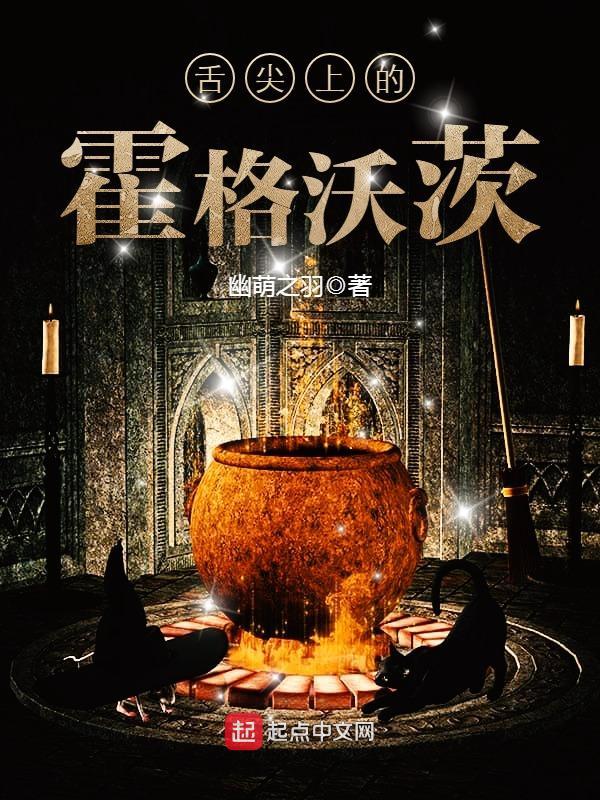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古代神捕类 > 第3章 初勘现场鬼神之说(第1页)
第3章 初勘现场鬼神之说(第1页)
王老五嘴上说着带林小乙去“见见世面”,实则刚拐出县衙大门,就把他当成了跟班小厮。
“去,前头‘张记’铺子,买三个肉馍,麻利点!五哥我起得早,还没垫肚子呢!”王老五摸出几枚铜钱,丢垃圾似的扔到林小乙怀里,自己则和李西晃悠到墙根底下,晒着太阳等现成的。
林小乙捏着那几枚还带着对方体温的铜钱,忍气吞声地小跑着去买。等他捧着热腾腾的肉馍回来,王老五和李西己经就着墙角一摊积水,拿了副破烂不堪的骰子,赌得唾沫横飞。
“快点!磨磨蹭蹭,馍都凉了!”王老五一把夺过馍,啃了一大口,油汁顺着嘴角往下流,含糊不清地指挥,“边上站着去,放风!看见师爷或者县尊大人过来,咳嗽一声!”
于是,林小乙就真的像个门神一样,傻站在巷子口,吹着冷风,看着那两个老油条蹲在墙根,一边啃着他买来的肉馍,一边掷骰子赌钱。他那份,自然是没人想起。
高逸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案发的黄金时间正在被这样无谓地浪费。苏府现场的任何痕迹都可能因为人为或环境因素而消失或改变!他心急如焚,却只能木然地站着,胃里因为没吃早饭而隐隐作痛,被泥水浸透的裤腿冰冷地贴在皮肤上。
也不知过了多久,王老五才输光了手里的铜板,骂骂咧咧地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走了!办正事!”
所谓的“正事”,就是在苏府周边几条街巷漫无目的地晃荡,遇到相熟的小贩或者店铺掌柜,就凑上去闲聊几句,话题三句不离苏府的“奇案”,重点打听有没有什么“生面孔”或者“可疑的人”。
“王哥,您这可难为我了,这南来北往的,哪天没几个生面孔?”
“嘿,听说没?苏家那是得罪灶王爷了!银子是贡品,收走啦!”
“可疑的人?我看苏家那个管家就挺可疑,眼珠子滴溜溜乱转……”
得到的多是些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闲话,甚至大半都是关于“灶王爷”的灵异传说。王老五却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附和几句,加深一下鬼神作祟的氛围。李西在一旁溜须拍马,说五哥出马就是不一样,消息灵通。
林小乙跟在他们身后,像个透明的影子。没人问他话,也没人需要他记录。他沉默地听着,高逸的专业思维却在自动过滤这些无效信息:目击证词需要交叉验证,谣言传播有其路径和源头,但这些对于初期锁定嫌疑对象,效率太低,近乎无用功。
他的目光更多地在扫视街面、墙角、排水沟。现代现场勘查中,外围搜索同样重要,可能会发现嫌疑人遗留的痕迹或丢弃的物品。然而,青石板路人来人往,即便昨夜真有什么异常,痕迹也早己被清晨的车马行人破坏殆尽了。
接近晌午时,一个衙役气喘吁吁地跑来找他们,说赵捕头让他们都回衙门,要汇总情况。
林小乙心里微微一紧。不知道赵头他们那边的勘查,有没有突破性的发现。
回到衙门公房,气氛比早上更加凝滞。赵雄坐在主位,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笃笃声。郑龙抱着胳膊站在一边,浓眉紧锁,显然也没什么好消息。吴文则坐在角落,面前铺着纸笔,上面画着些凌乱的线条,似乎是在模拟那个奇怪的脚印。
王老五一进门,立刻换上一副谄媚又苦恼的表情:“赵头,回来了!哎,跑了一上午,腿都细了,街面上都问遍了,都说没见着什么特别扎眼的外来人,倒是那灶王爷显灵的说法,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赵雄不耐烦地打断他:“知道了!废话少说!”他目光转向郑龙,“你那边呢?”
郑龙瓮声瓮气地回答:“盘问了一圈苏府的下人。护院说昨夜巡更没发现异常。厨娘婆子们都赌咒发誓没靠近小库房。就一个帮厨的小子,前几天偷吃祭品被管家罚过跪,还有个护院,欠着赌坊几两银子,有点嫌疑。但我看那怂样,不像有胆子一次偷百两银子的主。”
线索似乎一下子全都断了。密室、诡迹、毫无头绪的嫌疑人……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着整个公房。
“吴文,”赵雄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你那脚印,琢磨出什么没?”
吴文抬起头,推了推并不存在的眼镜(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头儿,这脚印确实蹊跷。我反复比量了,长约七寸,前掌极宽,足弓处却突然收窄,后跟反而又略宽些,形态非靴非履,更不像赤足。印痕边缘有湿泥扩散的痕迹,说明沾染的液体不少。”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最关键的是,灶台上只有这一个朝向门口的脚印,没有来的方向,也没有离开的痕迹,就像是……凭空出现在灶台上,又凭空消失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