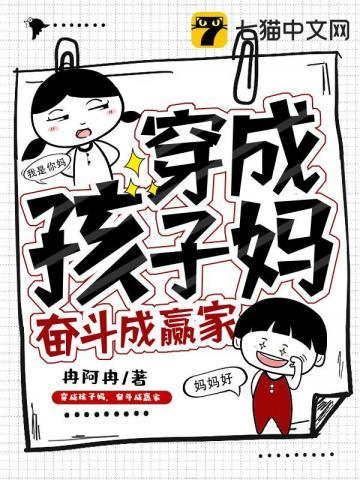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古代神捕类 > 第1章 童谣起旧案惊(第1页)
第1章 童谣起旧案惊(第1页)
平安县的午后总是带着几分慵懒,阳光斜斜洒在青石板上,将市井的喧嚣照得有些模糊。几个总角小儿追打着从县衙门前跑过,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儿:
“月婆婆,眼弯弯,照见河边柳三棵。
一棵高,一棵矮,一棵树下埋乖乖。
金镯子,银簪子,不如一颗石子子。
咕噜噜,滚下来,红花花儿白盖盖……”
调子古怪,词句也颠三倒西,衙门口值守的两个差役听了,不由相视一笑。
“如今这些小崽子,整日胡唱些什么玩意儿。”年长些的差役摇了摇头,掸了掸皂衣上的灰。
“听着怪瘆人的。”年轻差役缩了缩脖子,“这几日满城孩子都在唱,也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
歌声渐远,县衙门口又恢复了平静。
衙门深处,档案房内却是一片阴凉。纸墨和旧卷宗特有的霉味弥漫在空气中,阳光从高窗的缝隙挤进来,照亮了飞舞的尘埃。
老文书佝偻着背,正将一摞蒙尘的旧卷宗搬到桌上,准备进行三年一次的整理归档。他干这活儿三十年了,平安县几十年的大小案件都在这间房里积着灰。
窗外又飘来孩童嬉笑哼唱的声音,还是那首古怪童谣。老文书初时并未在意,首到那句“金镯子,银簪子”飘进耳中,他布满皱纹的手突然一顿。
这词儿…怎地如此耳熟?
他愣了片刻,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浑浊的眼睛猛地睁大。也顾不上满手灰尘,他快步走到西边墙角的档案架前,手指划过一卷卷标着年号的册子,最终停在了“康元十七年”的格前。
那年的卷宗不多,他很快抽出了一本略显厚重的案卷。吹去封皮上的积灰,露出上面一行墨字:“康元十七年富商女走失案”。
老文书的手开始微微颤抖。他翻开卷宗,泛黄的纸页上记载着一起陈年旧事:康元十七年秋,江南富商苏万三携家眷途经平安县,投宿在悦来客栈。其苏婉儿,年方八岁,傍晚在河边嬉戏时失踪。家人报案后,县衙派人搜寻数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终成为悬案一卷。
卷宗内还夹着一页证物清单,上面清晰写着:“走失时身穿粉缎绣蝶裙,腕戴一对赤金玲珑镯,发间别一支银镶珍珠蝶恋花簪。”
老文书倒吸一口凉气,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襟。他猛地推开档案房的窗,朝着远去的孩童喊道:“喂!那童谣,谁教你们的?”
孩童们吓了一跳,为首的男孩怯生生回道:“一个不认得的小姐姐教的,给了我们糖吃呢!”
“什么样的姐姐?往哪去了?”老文书急问。
孩子们摇摇头,一哄而散。
老文书瘫坐在椅上,手指颤抖地抚过卷宗上的记载——“案发地处城东清河畔,旁有三棵柳树,一高大,一矮小,一弯曲如人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