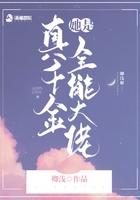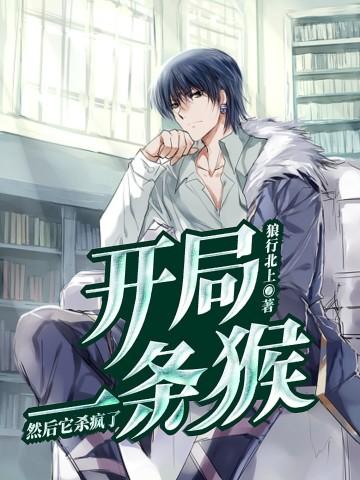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超级实用的直男恋爱技巧 > 160170(第2页)
160170(第2页)
“哪呢,哪呢?!”
“最后一名……”
刘昌邑定睛一看,第二百名果然是冀州府刘昌邑,一时间惊讶和喜悦涌入心头,激动得他热泪盈眶。
娘和师父总说他踏不下心去学习,明明他已经尽了全力,如今终于有了结果。
站在外围的陈青芸见他面色癫狂的从人群里挤出来吓了一跳,“这是怎么了?”
“我中,我中了,青芸我中了!”
“真的啊?”
刘昌邑拿袖子抹了把脸,“真的,吊车尾排在最后一名。”
即便是最后一名也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考不到的高度了,要知道每年参加乡试的人数都不一样,今年全国一共两万一千人参加乡试,明年还不知多少人呢,能考中的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
李氏道:“快回去把这个喜讯告诉亲家吧,他们肯定还不知道呢。”
二人坐上马车匆匆离开。
其他人继续站在外围等着看榜,随着围观的人渐渐散去,大家伙终于能上前。
李氏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侄儿的名字,失望的叹了口气,“禀辰已经考了四次,只怕过了今年就不会再考了。”
李家祖上出过三个举人,到了父亲那一代开始没落,如今过了五十多年竟再没出过一个举人……
不过儿子和青淮考中也是莫大的喜事,大家高高兴兴的回了家。
方菱一刻都待不住了,回去就把行李全都收拾好,只等明天一早就离开。
李氏和陈容帮她一起收拾东西,“还有两个多月就过年了,何不等过完年再走。”
方菱摇头,“过完年青淮还得去上京参加会试,一来一去又得耽搁小半年,还不知道樱儿的咳疾怎么样了。”
“你这一走,下次见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方菱放下手里的东西叹了口气,“说实话我也不想走,在这边住的这段时间是我这些年过的最轻松的日子了,不用管几个孩子吃喝拉撒,不用操心家里的琐事,不用担心相公的政务。”
“但当了娘这辈子就算是栓住了,离开孩子心里就惦记,想轻松都轻松不起来。”
姑嫂都明白她这话的意思,“只盼着咱们还有相聚的时候。”
“会的,青淮成亲你们可都得到场,谁都不行少。”
*
傍晚陈青岩和陈青淮二人才从府衙回来,二人得了知府的两幅字勉励他们会试继续努力,还有一块黄石砚和一盒徽墨。
东西虽然没有多贵,但意义不一样,这是他们读书以来第一次接触官场。
陈青岩倒是还好,陈青淮略微有些青涩,不过他年纪还小还得再历练几年才行。
晚上吃饭的时候,两人给大家讲了讲跟知府见面的事,“我们去的时候,大人正在写字,给我写的这幅是:不为外撼,不以物移,而后可以任天下之大事,给大哥写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知府倒是有点意思,送给陈青岩的那句话明显就是指出当年他被人诬陷,最后重振旗鼓一举夺魁的事。
陈青岩接道:“收下字后便拉着我们一起聊了起他当年的求学经过。”
林知府不是冀州本地人,他老家在益州,离着这几千里远。
益州作为比较落后的州府,教育资源极其匮乏吗,林家在当地还算是富裕人家,但想请个夫子都很困难。
因为他们住的那个县城一共只有四个秀才,其中两个年过半百了,书上的字都看不清,剩下的两个开了两家私塾,林知府便跟着其中一位秀才开的蒙。
因为天资聪颖,他十五岁便考中了秀才,来到益州府学读书,这里依旧没有多少读书人,府学只有一个举人教谕,而且年纪也不小了。
每次他去请教教谕问题时,都要提前跪在门前等候,等老爷子心情好了才能指点一二,心情不好跪上一天都没用。就这样努力求学最终才考中进士,坐到如今四品知府的位置。
临走时林知府还拉着二人道:“你们两个娃儿要好生珍惜读书嘞机会,争取会试更巴适,将来一起在朝堂上做官嘛!”
陈青淮学的惟妙惟肖,惹得大伙哈哈大笑。
王瑛摸着下巴心想,林知府益州人啊,现代应当是巴蜀那边,试验田里种的辣椒兴许他们会喜欢。
*
晚上吃完饭王瑛准备进试验田看看,今天白天突然弹出的升级消息都没顾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