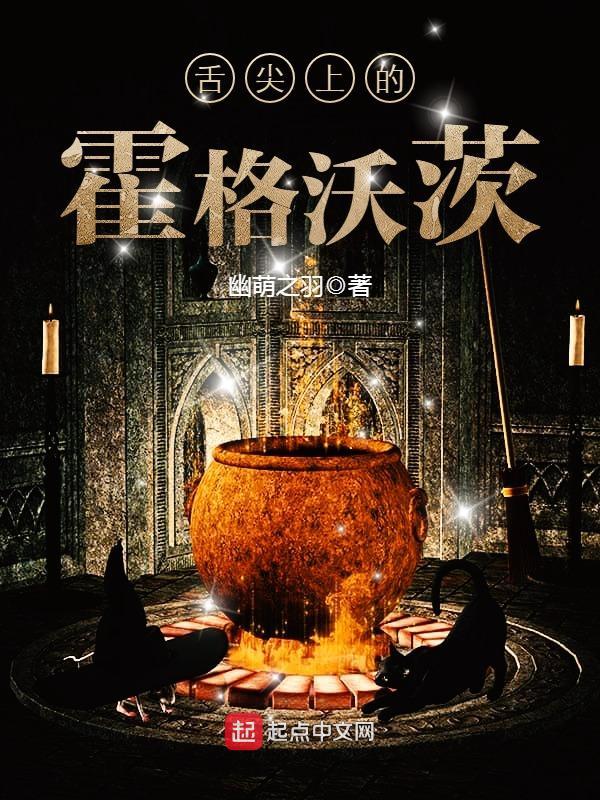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白日鬼依在(打一字) > 19阿涟(第2页)
19阿涟(第2页)
不知是性子的缘故,还是她没有记忆,阿涟对所有人都是怯生生的,听到一点动静就要躲藏起来,稍有人靠近就会缩着脖子躲闪。
第一次过年的时候,鞭炮声接连响了三日,第二日起就有许多人拜年。孙大娘是个寡妇,有不少靠人情帮忙的时候,在年节走动时就更注重礼节,历来都是要带两个儿子迎接的。
可这次孙郎却没有站在娘亲的身边,他在整个家里找了两圈后,终于拉开了偏房里一座大衣柜的门。
阿涟就这样哆哆嗦嗦和他对视,他穿着冬天滚了毛边的衣服,不由分说塞进来个汤婆子。“你干嘛躲在这里?”
阿涟摇摇头,她也说不清楚,为何这么害怕生人拜访,只是怔怔瞧着他脸上的红晕。
凑近瞧了她半天,孙郎拧着眉头想了片刻后,也挤了进来。
狭小的衣柜里,多出一个半大小子,空间都逼仄起来,阿涟不容抗拒的感受着他带来的暖意。
“我陪你躲着,你就不怕了。”
他在黑暗的衣柜里冲她伸手,笑着咧出两排大白牙。
阿涟果真就不怕了,外面的声音像是都被他的话语赶走,她伸手握住他,慢吞吞靠近。
那天他们被找到的时候,都已是傍晚,客人早都走了。孙大娘难免动怒,孙郎却站出来,说都是他要带着阿涟胡闹。
孙大娘罕见的教训了他,那一夜,他跪在祠堂面前挨板子,阿涟就在门外听了一下又一下抽打声。
“说,你错了没!”
“错就错了,你不能再怪阿涟!”
等领完罚的孙郎从祠堂里走出,见到她的第一反应,却是把打肿的手藏起来,挤着眉扮鬼脸逗她笑。
此后的一年,孙郎便执着于带她出门。给东村的人送篮子要拉上她,给医馆的大夫结药钱要她跟上,连去隔壁送针头都让她也一起。
逢人问起,孙郎就大大方方的笑着,把她拉到人跟前:“这是我家阿涟,好看吧?”
人们就会和和气气的冲她笑,再送她一把爱吃的饴糖。
久而久之,阿涟也可以一个人上街去,她以为果真是她讨喜,遇见的每个人都带着笑。直到一日孙大娘偶然托她买药,在街角转弯处,她瞧见了孙郎在给新搬来的人家分糖瓜。
少年人站在台阶下,认认真真开口:“我家还有个妹妹,她胆子小,过两日你们见了,千万对她好些。赶明日,我再来帮你们搬东西!”
一切恍然,原是有人在为她上心。
阿涟本以为,她就会这样在孙家长长久久的住下去,陪孙大娘针织煮茶,和孙郎嬉闹游玩。
直到一日邻人和孙大娘闲坐,打趣的看着远处斗蛐蛐的阿涟和孙郎,“你还愁什么找媳妇,要我说,阿涟不就正配吗?”
阿涟听到了,托着下巴小声问:“媳妇是什么?”
“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孙郎催着自己的蛐蛐往前,“是他最重要的女子。”
手中的草根就停下来,阿涟歪头,注视着他头顶,“你也会有吗?”
“当然会有。”孙郎随口回答,他还紧盯着两只蛐蛐,原本他的要输,可阿涟一跑神,他的蛐蛐顺势而上,“我赢了!”
兴奋欢呼,却没听到如往常为他喝彩的声音,孙郎抬头,这才瞧见她若有所思的神色。
端坐起来,孙郎看着她的眼睛,突然发问:“阿涟,你要做我的媳妇吗?”
猛然瞪大了眼睛,阿涟慌张的想解释,她愣神只是没想到会有人比她对他还重要,可话出口又觉得不对,支支吾吾几下后,先瞧见了他眼中自己通红的脸颊。
短短两年,孙郎却抽了条,少年面孔展开,俊朗挺拔的像是春日发芽的杨树。
心就在此刻漏了一拍,咚咚咚的,跳了一整天。
——
“后来呢?”
许枝影着急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