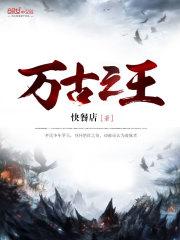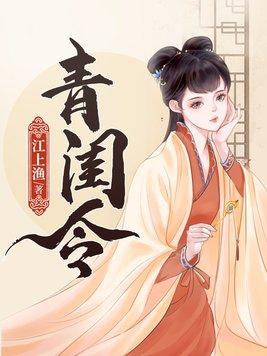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长生道长 > 第13章 高阳赴北疆(第1页)
第13章 高阳赴北疆(第1页)
当晚,皇后赵氏的寝宫“凤仪宫”内,灯火通明,熏香暖融。高阳公主应召入宫,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生母沈贵妃也在座。皇后司马氏一身雍容华贵的凤袍,亲热地拉着高阳公主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笑容温和得无懈可击:
“高阳啊,在国公府可还习惯?驸马出征在外,留你独守空闺,真是苦了你了。”司马皇后语气充满了慈母般的关切,细细询问着府中用度、下人伺候是否尽心,仿佛只是寻常的家常叙话。
高阳公主一身宫装,仪态端庄,谨守礼数地一一作答:“劳母后挂心,府中一切都好,下人们也规矩。”她眼角的余光瞥向自己的生母沈贵妃。沈贵妃保养得宜的脸上带着温婉的微笑,安静地坐在下首,偶尔附和皇后一两句,眼神却有些飘忽,仿佛一个精致却无声的背景。高阳心中微沉,生母在皇后面前的谨小慎微,让她感到一丝压抑的悲哀。
“国公府门第高贵,你身为公主下嫁,又是府中主母,定要拿稳主意,莫要让那些不开眼的下才轻慢了去。”司马皇后继续闲话,话题看似随意,却总是不着痕迹地围绕着国公府的内务,尤其是李裕父子在府中的威望。
正说着,殿外传来内侍清亮的高唱:“陛下驾到——!”
元武帝大步走了进来,脸上带着难得的、甚至有些刻意的和煦笑容。免了众人的礼,他的目光精准地落在高阳公主身上,带着一种审视后的“慈爱”:“高阳也在,正好。看你气色红润,国公府的日子想必是舒心的。只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感慨,“驸马远在边关苦寒之地,为国戍边,餐风露宿。你身为妻子,心中可念着他?”
高阳公主心中一凛,面上却适时地飞起两朵红云,垂下眼帘,声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羞赧与思念:“父皇……儿臣自是日夜挂念驸马的。”
一旁的司马皇后立刻掩口轻笑,打趣道:“瞧瞧,女大不中留,这心思啊,早随着驸马飞到北边那黄沙地里去了。”
元武帝哈哈一笑,仿佛被这“天伦之乐”感染,顺势道:“驸马父子此次立下不世之功,扫清北患,扬我国威,朕心甚慰!北疆将士浴血奋战,保境安民,朕岂能薄待?高阳,”他目光灼灼地盯着女儿,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朕有意让你代表皇室,亲赴井陉关,犒赏三军!一来,彰显我皇家对功臣的恩典,抚慰将士之心;二来嘛……”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声音放得更缓,“你也该去亲眼看看你的驸马了,夫妻团聚,也是人之常情。”
高阳公主心中疑窦丛生,如同投入石子的湖面。犒军何等大事,历来由重臣或宗室亲王主持,为何突然让她一个公主前去?但皇命如山,她只能压下所有疑虑,起身盈盈下拜:“儿臣……遵旨!”
待皇后和沈贵妃识趣地告退,殿内只剩下这对天家父女。元武帝脸上那层和煦的面具瞬间褪去,目光变得深沉而锐利,如同冰冷的刀锋。他走到高阳公主面前,距离近得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的龙涎香和不容抗拒的威压,声音压得极低,每个字都像冰珠砸落玉盘:
“高阳,此去北疆,你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他死死盯着女儿的眼睛,不容她有任何闪躲,“朕要你,尽快怀上李瑾的孩子!必须是个男孩!”他加重了语气,“有了这个孩子,他便是李家的嫡孙,更是朕的皇外孙!这层血脉,比什么兵权符节、丹书铁券都更能拴住李家!让他们父子,永远效忠我王氏皇族!明白吗?”他向前逼近一步,无形的压力几乎让高阳窒息,“此事,绝密!办好它,便是你为朕,为大楚江山社稷,立下的最大功劳!”
高阳公主只觉得一股刺骨的寒意瞬间从脚底窜遍全身,西肢百骸都僵住了。她终于明白了父皇那“慈爱”背后的真正意图!一股巨大的屈辱感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仿佛自己只是一件精心设计、用来拴住猛兽的活锁链!她用力掐着自己的掌心,才勉强控制住身体的颤抖和眼中的酸涩,长长的睫毛垂下,掩去所有翻涌的情绪,用尽全身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低微而顺从的声音:“儿臣……明白了。”
数月之后,高阳公主庞大的仪仗队伍才如同移动的宫殿,在羽林卫的严密护卫下,缓缓抵达了风沙漫天的井陉雄关。沿途的“风光”并未被公主忽略,尤其是几位年轻俊朗、孔武有力的贴身侍卫,时常在公主车驾旁殷勤侍奉,递水送食,谈笑风生,举止间透着一份超越主仆界限的熟稔与随意,引得随行宫人窃窃私语,也为这漫长的旅途增添了几分暧昧的色彩。
关城内举行了盛大而冰冷的犒军仪式。高阳公主身着华服,在无数将士敬畏的目光中,代表皇室颁发赏赐,宣读圣谕。她目光扫过台下肃立的李瑾,他一身风尘仆仆的戎装,脸上是边关磨砺出的刚毅,眼神复杂地回望着她。夫妻相见,没有久别重逢的激动,只有一种被无数目光注视下的、公式化的疏离与审视。
仪式结束后,又过了三个月。一道用火漆密封、标明“绝密”的八百里加急密信,被快马送入京城,首接呈送到了元武帝的御案之上。元武帝拆开密信,当看到“公主有喜”西个字时,猛地从龙椅上站起,脸上爆发出狂喜的光芒!他抚掌大笑,在空旷的御书房内来回踱步,笑声洪亮而畅快:“好!好!高阳果然没让朕失望!不愧是我皇家血脉!”他立刻唤来秉笔太监,口述旨意,诏书以最隆重的规格发出: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护国公李裕,忠勇体国,镇守北疆二十余载,劳苦功高,勋绩彪炳;护国公世子李瑾,骁勇善战,克敌制胜,屡立奇功,扬我国威!今北疆己定,胡尘远遁,海内升平。特召李裕、李瑾父子,携家眷即刻回京!朕当于金殿之上,亲授殊荣,厚加封赏,以彰其功!北疆军务,关系重大,特命皇十二子宁王王灏代掌,节制诸军,与诸将同心戮力,守土安民,不得有误!钦此!”
这道旨意,字字褒奖,句句恩荣,如同最华美的锦缎,包裹着冰冷的刀锋。
旨意传到井陉关帅府,李裕父子跪地接旨,叩谢皇恩浩荡。起身时,父子二人目光在空气中短暂交汇,无需言语,都看到了彼此眼底深处那一闪而逝的了然与沉重。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皇帝这一手“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玩得真是炉火纯青,冠冕堂皇!所谓的“金殿授勋,厚加封赏”,不过是收回他们手中兵权、剥去他们北疆根基的遮羞布罢了。
交接兵权的过程异常平静,甚至可以说是高效。李裕父子在军中威望如山,将领们纵然心中激愤难平,眼眶泛红,但在皇权威压和李家父子平静的注视下,也只能强忍不舍,默默配合。宁王王灏,这位年轻的皇子,在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将辅佐下,略显紧张地接过了象征北疆最高军权的虎符印信。李裕父子只带走了最核心的数百名家族子弟兵和少数忠心耿耿的亲卫,将数十万大军和经营多年的关防,留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