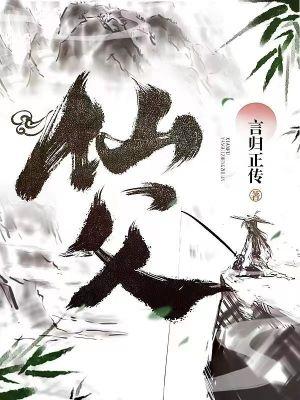北仑中文网>末世余生cg > 第13 章 人类社会重构(第1页)
第13 章 人类社会重构(第1页)
尸潮退去后,曾有好事者评估:这座曾经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幸存者或许仅存一两万人。这个数字如同冰锥,刺穿了任何关于“文明延续”的微弱幻想。
米面粮油,崭新的衣物,未拆封的卫生用品、整箱的瓶装水、甚至一些奢侈品……这些在文明社会里代表便利与享受的东西,此刻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构成了一个悖论般的现实:生存所需的物资总量,对于仅存的一两万幸存者而言,竟显得“极大丰富”。
然而,这种“丰富”,并未带来共享与和平。
起初,突然失去国家机器、法律、道德约束……这些维系社会的无形框架,一个个微小的幸存者团体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悄然萌发。他们通常只有几人到十几人,成员之间往往有着天然的信任基础:一家人、几代亲朋、患难与共的情侣、或者像陈默他们这样,在绝境中相互扶持走到一起的陌生人小团体。
张卫国对此有着最朴素的见解,他一边用磨刀石打磨着消防斧的刃口,发出刺耳的“嚓嚓”声,一边对同伴们说:“这世道,爹娘老婆孩子都未必靠得住,更别说外人了!信谁?就信跟你一个锅里搅过马勺,一起挨过饿、杀过那玩意儿的人!”他浑浊但锐利的眼睛扫过陈默、苏晴、林晚,“咱们西个,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个窝里的狼崽子!”
这种基于极度亲密关系的小团体模式,成了末世初期的绝对主流。他们像警惕的鼹鼠,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巢穴。林晚家所在的这栋楼,就是这样一个精心构筑的“鼹鼠洞”。入口被各种杂物巧妙地伪装和堵塞。
在这种高度戒备下,形成了类似于一种“黑暗森林法则”的生活状态。所有小团体都怕自己被伤害,所有小团体都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潜行于废墟之中,竭力隐藏自己的踪迹——熄灭不必要的火光,控制烹饪产生的烟雾,专门找一个房子丢生活垃圾,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搜寻物资。
往往两个小团体之间彼此发现了对方,选择的是远离,而不是交流。尽管受伤害只是想象中的……
“永远不要高估陌生人的善意,”就连团队的智囊苏晴也是这样认为的,“无政府状态会把人变成最可怕的野兽。我们需要的物资,从无主的废墟里找,比从活人里‘拿’,风险小得多。”她将搜集到的药品仔细分类,贴上标签,动作一丝不苟。
---
这样的社会结构使人类度过了原有社会崩塌的阵痛期,或者说是迷茫期…
当人们渐渐适应,一种新的力量开始在废墟的阴影中悄然汇聚、膨胀——大型幸存者团体。
它们如同废墟上野蛮生长的藤蔓,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驱动它们形成的核心动力,是**力量**。
人多,意味着更强的搜寻能力,可以覆盖更广阔的区域,获取更多、更稀缺的资源(尤其是药品、燃料、武器和大型庇护所)。
人多,意味着更强的防御能力。可以构筑更坚固的工事,组织起有效的轮值警戒,甚至主动出击清剿威胁(丧尸或其他敌对团体)。
人多,意味着更强的威慑力。在黑暗森林中,个体或小团体是猎物,而拥有几十甚至上百名武装成员的团体,则成了猎人,甚至是划定地盘的领主。
人多,还意味着分工的可能。战士、搜寻者、工匠、医生、管理者……专业化的雏形开始出现,效率得到提升。
这些大团体的形成方式各异。有些是以某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为核心,凭借其个人魅力、武力或资源,吸引并整合了周边零散的小团体和幸存者。这类领袖往往带有鲜明的枭雄色彩,手段强硬,赏罚分明。
另一些则是由多个原本就有联系或面临共同威胁的小团体主动联合而成,通过推举代表或建立某种松散的议事规则来运作,初期可能更民主,但也更容易陷入内耗。
还有一些,其底色则更加黑暗和赤裸——它们本身就是由最凶狠的掠夺者集团发展壮大而来。通过武力吞并、恐吓收编、甚至首接屠杀和奴役弱小团体,如同滚雪球般迅速膨胀。这种团体的核心信条就是弱肉强食,内部等级森严,充满暴力压迫。
无论哪种方式形成,这些大团体一旦站稳脚跟,其行为模式都惊人地一致:**扩张与掠夺**。
“听说了吗?东边‘钢铁厂’那帮人,前些天把‘老粮库’给平了!”一次外出搜寻归来,陈默无意间说起了这个八卦。“老粮库”是盘踞在城东一座废弃国家粮库的小团体,据说有二十多人,依托坚固的粮仓和存粮,日子过得相对安稳。
“平了?怎么平的?”张卫国漠不关心的随便一问。
“说是‘钢铁厂’的人看上了粮库的围墙和里面的存粮,派人去谈‘合并’,老粮库的人不干。结果没过两天,晚上就出事了。”“有人远远看见火光冲天,枪声跟爆豆子似的响了大半夜……第二天再去看,粮库大门被炸开了,里面……里面全是血,没几个活口了。剩下的听说都被‘钢铁厂’抓回去当苦力了。”
陈默沉默地擦拭着撬棍上的污迹,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苏晴正在给林晚手臂上一道搬运物资时划破的伤口消毒,闻言动作顿了一下,眼神变得更加冰冷。
“钢铁厂”是盘踞在城西废弃钢厂的一个大型团体,据说核心成员就有五六十人,依附他们的外围人员更多,以凶狠好斗、装备相对精良(拥有自制火器和炸药)著称。他们的“领地”意识极强,不断向西周辐射影响力,吞并或驱逐附近的小团体。
“还有南边那个‘互助会’,”陈默继续补充道,语气带着一丝讽刺,“名字叫得好听,说是大家互助互利。可他们划的地盘越来越大,凡是他们看上的小区,要么‘自愿加入’,要么就得按月上缴‘保护费’,粮食、药品、燃料……什么都行。不交?他们就派巡逻队‘清理’,轻则抢光,重则……”他没说下去,但意思不言而喻。
这种“清理”行动,陈默小队也曾远远目睹过一次。那是在搜寻一个靠近“互助会”宣称势力范围的街区时。隔着两条街,他们看到一栋居民楼里冒出滚滚黑烟,伴随着零星的枪声和凄厉的惨叫。几个惊慌失措的人影从楼里逃出,没跑多远,就被后面追出的、穿着统一深色服装(用油漆在旧衣服上涂了标记)的人追上,棍棒和砍刀毫不留情地落下……陈默他们立刻隐蔽起来,绕了很远的路才返回。
这些大团体如同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废墟之上。他们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巡逻制度,构筑防御工事(利用废弃车辆、建筑垃圾堆砌路障,在关键位置设置瞭望塔)。对于区域内残留的小团体,策略简单粗暴:要么臣服加入,要么缴纳高昂的“贡品”换取暂时的安全,要么就被彻底“清理”掉。
小团体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放弃来之不易的独立和安全,加入一个可能充满压迫和未知风险的大集体?还是冒险继续在夹缝中挣扎求生,时刻提防着来自同类的致命獠牙?
好在陈默他们所在这个区域,物资相对没那么丰富,范围巨大,还没有强力势力“”进驻。
---
然而,就在这看似彻底滑向丛林法则的无序深渊中,一种意想不到的、带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开始在几股强大势力相互角力的边缘地带,悄然萌发——**集市**。
它的出现,并非源于某种崇高的理想或重建文明的自觉,而是源于最底层的、无法被暴力完全扼杀的现实需求。
再强大的团体,也无法生产所有需要的物资。一个以战斗和掠夺为主的团体,可能缺乏熟练的工匠来修复武器或工具;一个占据了大片住宅区的团体,可能急需药品却囤积了大量无用的衣物;一个拥有技术人才(如医生、机械师)的团体,可能严重缺乏食物或燃料。
最初,这种需求只能通过偶然的、充满危险的“黑市”交易来满足。一些胆大包天、熟悉城市地下通道或隐秘路线的“独狼”或微型团体,充当起了风险极高的“货郎”。他们像鼹鼠一样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穿行,将A地富余的药品偷偷运到B地,换取C地急需的弹药或工具。交易地点往往选择在废弃的下水道交汇处、坍塌建筑形成的隐蔽角落,或者约定俗成的、远离各方巡逻路线的废墟中心点。交易过程快如闪电,双方戒备森严,一手交“货”,一手交“物”,绝不废话,也绝不留恋。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巡逻队撞见,或被交易对象黑吃黑。
这种交易方式效率低下,风险极高,流通量极其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复杂化的需求。
渐渐地,一些实力最强、统治相对稳固、且其领导者具备一定远见(或者说,看到了控制交易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大型团体,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模式:在其势力范围的核心区域或边缘缓冲区,划出一块相对“安全”的区域,建立起**受其保护和管理的集市**。